触
这是一个平静的夜晚
树以独特的姿态站立
保持着亘古不变的距离
而我们却被一种呼唤诱惑
走到一起
嘴唇在黑暗中颤动
情欲之火呈暗蓝色
焚毁我们苍白的面具
就这样我们穿过
时间和记忆
穿过树与树之间的距离
双手相握
面前是一片复活的土地
圣水顺阔大的叶片滑落
蝙蝠从欲望的头顶
无声掠过
嘴唇是缄默的
我们用眼睛对话
一种兴奋和不安
将我们淹没
另一种语言
诞生于黑暗
女人是房子
我进入女人 在夜晚
我无法拒绝温暖的诱惑
进入她的内部
她的乳房耸入夜空
似教堂神圣的穹顶
我在她的内部做梦
陷入幸福之中
我在她的内部衰老
任一种不可捉摸的火
将我悄悄毁掉
走廊
不知道是从哪扇门走进来的
走廊长长的
墙壁被雪白的布蒙着
头顶上的灯发出蓝幽幽的磷光
我想我不久就可以走出
这道长长的走廊
我想象走廊尽头一定有一个花园
开着些紫色的小花
有几个小姑娘在那里嬉戏
唱着德语歌
走廊长长的看不到尽头
四周死亡一般沉寂
脚敲在地板上发出可怕的回声
我发现走廊两旁都是些病房
病房里躺着一些没有面孔的病人
他们笔直地躺着
不发出一点声息
我想我不久就可以走出
这道长长的走廊
我想象走廊尽头一定有一个花园
我可以在那里和一些小姑娘嬉戏
在开紫色小花的的草地上躺上一个下午
让那些小姑娘把揉碎的花瓣
撒在我的身上
走廊里灯光更加暗淡如同鬼火
袭人的寒气使我呼吸艰难
我加快脚步走着
最后狂奔起来
这时一个穿白制服的没有面孔的人
出现在我的面前
他猛地一把把我推进身旁的一间病房
接着把我按到一张床上
然后无声无息地走了
门在他的身后无声无息地关上
一张白色的床单压在我的身上
使我动弹不得
啊,我的面孔也没了
情话
亲爱的别作声 在任何时候
对这世界都不能掉以轻心
关于那只十二月三十日
被一个矮墩墩的老家伙
砍落的手
(晚报说那只手手指细长)
它会不会攀着窗台上来
在窗帘上留下一些血迹
使我们的安眠药失灵
关于这里的一切 诸如天气预报
空中飘过来的一根羽毛
傍晚六点钟 沈举人巷出现的
一个陌生面孔的男子
以及拉萨来信
以及信上被划掉的一行
以及正在流行的艾滋病之类
我们都不能掉以轻心
亲爱的 别作声
这夜晚多么宁谧
请把脸贴近我
让我吻吻你
你的嘴唇总有一种清香
如故乡的一片苜蓿花地
亲爱的 别作声
这夜晚多么宁谧
愿我们做个好梦
别总想着明天
该撕去一张日历
手术
麻醉济从我的神经上经过
一种凉丝丝的快感
我闭上眼
如同即将灭亡的人
在主刀医师和他的实习生面前
我是一具难得的标本
二十多年生活养育的肉体
有病 然而不失新鲜
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动刀了
我在麻木的大脑皮层下等待着
高超的技巧
一块肉轻而易举地脱落
白色的切口处 血涌出
他们从我的伤口上获得知识
他们会不会把我的心脏
一起摘除 连同大脑
假如他们兴奋得忘记
我是一个活人
高翔或者野村
其实我的名字并不重要
它们并不能改变什么
也并不能说明什么
我背井离乡
穿过一座座城市
每座城市都是一样
人们忙忙碌碌
在大街上行走
手里抓着钱包
我的名字对他们并不重要
有时 我的脸上浮起微笑
想同身旁的人打声招呼
表示友好
可我的手臂总是很沉
难以举起
夜晚我在大街上散步
想唱支歌
想和谁谈谈
街上很冷清
只有影子在路灯下陪伴我
为了让我高兴
它一会儿落到身后
一会儿又转到面前
我低着头
偶尔有一只狗轻手轻脚
从我的身边经过
或走到前面不远处停下来
回头看我一眼
或一直朝前走
头也不回
好象去赴一次重要约会
弥留之际
黑暗中你来到我的身边
我听到你的脚步
象飘落的叶子
我已寻你一生
你来了我就不再孤单
虽然看不到你的面孔
但却能听到你的声音
感觉到你手指的触摸
不久我就要离去
你会为我送行
你的嘴唇轻轻贴着我的额角
冰凉而真实
一杯咖啡
我们喝完这杯咖啡
却并不能说出它确切的味道
这杯咖啡 也不会
让我们记起多少过去的事情
或对未来作更多的设想
不过 这是一杯不错的咖啡
在三流咖啡厅黯淡的角落里
喝完它
使我们更易于适应眼前的境遇
适应女招待涂得血红的嘴唇
它丰厚而滋润
并没有确切的含义
总之 一杯咖啡就是一杯咖啡
你喝它时称它为咖啡
有时把自己和方糖一起融入杯中
喝下去时不过还是一杯咖啡
赛里木湖
我走向你 赛里木湖
黄昏时分你清澈平静
如同一面光滑的镜子
映照出一方古铜色的天空
和远山倒立的黑影
我看到你白色的灵魂
在水底缓缓地游荡
多年前我就想走向你 赛里木湖
想坐在你的身边
和你作一次亲密的交谈
想和你融汇于一体
静静地依偎在大山的脚下
与草原在一起
与沙漠在一起
与永久的孤独
在一起 在孤独之中
在陈旧而空洞的苍穹之下
看黑暗怎样一次次从大山背后升起
听歌声于自己的心底发出
赛里木湖 你躺在高原之上
你不仅仅是沉默的水
屈原
忳郁邑余侘傺兮
吾独穷困乎此时也
——《离骚》
你对天空说完最后一句话
便把自己沉入水中
汩罗江没有言语
让柔软的水藻涤你的长缨
涤你的十指和洁白的嘴唇
你的鸾车已随天上的云飞逝
你怀中的秋兰和白芷还在
香气由你的骨殖中透出
使汩罗江水变蓝
使水中的岩石变得柔软
鱼类从你的长衫下游过
晃动着宽宽的尾鳍
它们不知道你是三闾大夫
没读过你的《桔颂》和《离骚》
也不知道你是个爱美的疯子
为寻绝世绝代的美人而来
它们用殷红的小口
啄食你的眼皮
象啄食花瓣一样
鲁迅
人们沉睡的时候你走出来
从空气做成的屋子里
你一身洁白
在黑夜里发出微光
在另一个世界上
你再也不能说话
天空在你的头顶诡秘地变幻
从闰土钢叉下溜掉的那只猹
远远地坐着看你
绿茵茵的小眼睛
闪出几分凄清
地上的野草又黄了
你站在空气背后
你知道下一步将发生什么
一切都在预料之中
正象你的后院里有两颗树
一棵是枣树另一棵还是枣树
正象你在天亮前必须离去
走进你空气做成的小屋
你一身洁白
在黑夜里发出微光
而所有的人都没有觉察
你们需要睡眠
张志新女士
你以怎样的步履迈向死亡的边界
以怎样的目光面对古老沉睡的土地
没有嘴巴的土地
面对风中静默的向日葵 白杨树
一年一度死去又复生的野草
你以怎样的微笑和泪水告别
现在你与矿物 石头和水在一起
你坐在无人到达的深处
把双手浸泡在水中
让水顺着手臂浸透你的全身
你在自由与真理的祭坛上死去
但你没有升入天堂
你也不祈求升入天堂
你只梦想从你的手指上开放一朵小小的花
让你嗅一嗅春天的气息
现在人们不再谈论你了 对许多人来说
你已遥远得近乎一种从未存在过的物质
你喉管的那一声断裂
已化为风化为夜间生灵们的浅唱
你身躯内流下的女性的血
已经和田野和庄稼融为一体
然而在自由与真理的祭坛前
无畏者的鲜血仍在流淌
夜里的事件
死去的人成群结队
于昨夜出现
他们面目阴郁
嘴里发出唧唧之声
整个夜晚我跟随他们
我看到这些白色的亡灵
象潮水
沿着大街流淌
我看到他们经过一片街区
又一片街区
用长长的指甲
在每一扇窗子上
刻下白色的符咒
死去的人在天亮前离去
在大街上留下许多头发和牙齿
死去的人有一天还会来
也许不再离去
大街
大街横躺着 没完没了
裹尸布一样苍白陈旧
各种各样的鞋底在上面嘶叫
印下肮脏的足迹
一个疯狂的女人在大街上狂叫
她将胸罩抛给好色的行人
将内裤撕成碎片
赤身裸体奔向广场
以她最后的策略对付世界
很多年我被大街困绕着
逃不出假象编织的罗网
廉价的阳光照亮我的脑门和思想
那些摇摇晃晃手持水果刀的人
构成我的空气
他们的身上散发出同样的汗臭
或雪花膏的气味
表情相似的面孔仿佛可以撕下来
随处张贴
夜晚 大街斯斯文文地躺着
如纯洁温良的处女
我是大街上一位久病不愈的夜游者
我总在担心 有那么一天
身上会长出蹄子和尾巴
逃亡
这些年 迫于生活
我不得不学会各种方式的逃亡
从满腹经纶的长辈
或智慧超群的胆小鬼那里
获得宝贵的经验
不管他们是否有脚气
哮喘 或夜尿症
逃亡是一种迫不得已的生存技巧
正象秋天的大雁掠过凄凄寒夜
向南方逃亡
在撒谎成癖的人群中
我借助谎言逃亡
在不便直立行走的时候
我装扮成四脚动物逃亡
更多的时候我以假想的翅膀
向天空逃亡
直至从粘糊糊的黑暗中坠落
摔得遍体鳞伤
如今我开始向自己的肉体逃亡
它是我最后的堡垒
一座温暖而可靠的坟墓
市场
一把闪亮的刀在空气中转动
避开飞舞的苍蝇
各种动物的肉 猪的或牛的
被切割成条状
这一切发生在惊心动魄的嚎叫之后
新鲜的肉冒出丝丝白色的热气
持刀者正把它们转化为货币
我们必须有充分的心理准备
习惯这种屠杀和肢解
习惯白胖的手指的利落
它撕扯猪肠子象撕扯一截绸带
我们不必要求他们慈悲
在这些持刀者眼里
再漂亮的动物也不过是一堆肉
年轻迷人的家庭主妇
穿梭在各种肉和肠子之间
她们挑选那些看相好的肉块
肝 肠子或心脏
她们有义务将这些血淋淋的商品
烹饪成可口的食物
使她们的先生满意
只是不要让她们去屠宰场
这些胆小的家庭主妇
假如她们看到那那些活蹦可爱的动物
怎样在屠刀下嚎叫着倒下
市场必定萧条
最后我们有责任提醒城市规划人员
屠宰场必须隐蔽
而且离市场越远越好
看戏
让我们象傻子一样再欣赏一次吧
多年来 我们每看一场戏
脖子总要被拉长一次
那只摆布我们的手
藏在黑暗之中
大红绸缎的幕布在目光的焦点处开启
道具分布在既定的位置
我们细致阅读从后台登场的
每一张面孔
它们表情诡谲 被灯光粉饰
仿佛在水面上漂浮着
在各种各样的面孔当中
有时会漂浮出那么一张失血 苍白
接近死人的面孔
它令我们不快
引起皮肤过敏
或连续三个夜晚的恶梦
这大抵是戏剧实施教化功能的
一个方面的成功
但更多的是快乐的面孔
滑稽和夸张的表情
使台下爆发出咯咯咯的笑声
使大部分观众因快乐而面孔抽搐
这些快乐的面孔组合成一台戏
人们称之为喜剧
一次我在人群中欣赏一台戏
易于冲动的观众挥舞胳膊
向大明星叫好
而拳头却砸在我的鼻梁上
我无辜充当了戏剧的牺牲品
我差点对着舞台大喊
你们表演得够精彩得啦
不过要适可而止
炎热的夏天
用什么样锋利的刀能劈开
粘乎乎的空气
这些滚烫的分子和原子
在撞击和压迫我们的肺
以及感觉神经
我们的伤口不断溃烂
正沦为苍蝇的食品
死去的人苍白的面孔
在空气中显得悲伤而模糊
而酷热的阳光依然在头顶倾泻
象炼钢厂的火焰
将我们烘烤
我们已经嗅出身体的肉香
夹杂着汗臭
大地上干渴的树卷曲起枝叶
静止不动 如同死去
在刺目的天空下
鸟的翅膀笨拙地扇动
仿佛不是在飞翔
而是爬着前进
它们也许即将坠落
或燃烧
我说阿夏
我说阿夏你瞧这傍晚的天空多美
你瞧这平缓的小山多美
我说阿夏我嗅出一股清香味儿
它使我想起童年我说阿夏
你可不能总是低着头我说阿夏
既然你说不出更爱他还是更爱我
就是说你是可以爱我的 我说阿夏
干嘛死心眼儿那家伙走了红运
看到我们一副神气劲儿真让人呕心
我说阿夏既然阿狗已背弃了我们
他就不再是我们的朋友
我说阿夏你干嘛低着头你那时可不是这样
我说阿夏你小的时候可是个爱笑的女孩
那时你一笑起来就没个完
拚命扯住自己的头发
那时候你还是个黄毛丫头
你一头黄发笑起来就没个完 泪水从你的眼角笑出来
弄得我也笑出泪来 当然还有阿狗 我说阿夏
那时我们经常溜出黑洞洞的城门去看乡村的风景
我们穿过一片大麦地那是一个夏天
我们穿过一片大麦地豌豆花开得正香
有许多蝴蝶在麦地里飞上飞下
我说阿夏那时我们玩得多好我说阿夏
那时阿狗那小子可不坏还挺害羞
经常带点洋玩意给我们开开眼界
也让我们进过两次他家的洋楼
那洋楼很少有人能进去围墙上爬满开紫花的青藤
我说阿夏你那时一进那洋楼小脸就吓得苍白
你说你再也受不了了以后我们就不再去了
我说阿夏阿狗那小子长得比我英俊
你不得不承认阿夏你对他总是比对我好点
我说阿夏那次穿过大麦地你一定没有忘记
我说阿夏你采了许多豌豆花缠在头上
我说阿夏你好漂亮呀你咯咯地笑了
我也笑了当然还有阿狗
后来我们走到一个小池塘边我们一起玩水
我说阿夏那时你真疯啊玩起水来可真疯啊
把裙摆全弄湿了把满身弄得都是泥巴
结果不敢回家了走到城门口的时候呜呜地哭起来
你说我怕我怕哭得好伤心我说阿夏你别哭
哭可顶不了什么用
你还是呜呜地哭着哭得越发伤心了
女孩子都是这样
我说阿夏那次我们玩得真痛快
那次你采了许多豌豆花缠在头上
我说阿夏你好漂亮呀你咯咯地笑了
你可不能总是低着头我说阿夏
你可不能因为阿狗变成哑巴我说阿夏
没有阿狗我们也得活下去我们也得唱歌也得笑
阿狗充其量不过是阿狗我说阿夏
让我们谈点什么吧就说这些山吧我说阿夏
这些山这些平缓的小山充满了女性的美丽
我说阿夏这些山在黄昏里充满了玄秘的精神
这种精神你我都无法说清
而恰恰是这种精神把我们整个儿笼罩其中
我说阿夏你该抬一抬头吧我说阿夏
这大麦地好象还是从前的大麦地我说阿夏
这豌豆花开得多水灵多生动要是那时的你
在这里一定要咯咯地笑了
一定要采许多豌豆花缠在头上
我说阿夏当然现在你已不是孩子你伤心的时候
再也不会呜呜地哭了我说阿夏不哭就不哭吧
可低着头不说话总不是一回事我说阿夏
你瞧天快黑了我们该回去了
该走回那座有黑洞洞城门的城市了
这大麦地好香我说阿夏天快黑了
这大麦地将在夜的怀抱里睡去了
将象温顺的婴儿一般躺入土地的永恒之梦
我说阿夏没有阿狗我们也得活下去
也得从城门下进进出出象一种必须
也得粗鲁地挤巴士痛苦或甜蜜地陷入一重重情欲之网
也得把几枚小钱捏在手里厌恶而不能扔掉
也得生儿育女在周末闲聊三个小时随后睡觉
我说阿夏你倒是说话呀天快黑了我们该回城了
你老低着头总不是一回事儿
我说阿夏这大麦地好香
平淡生活的叙述
许多个日子平静地过去了象置身于吗啡液中
整个身子酥软成一块面包女人坐在身边
那种眼神是温情的没准她想啃我几口
她抱着房东太太的那只猫坐在我的身边
她哼着小曲这已成了她的习惯
她不停地翻弄着猫的一只耳朵
弄得那只猫懒洋洋的在她的膝上打呵欠
她出生在一个山洼里童年孤孤单单
每天独自一人爬到山顶上玩耍
山上的花很多她随便摘一些胡乱插满一头
有时伤心起来便放声嚎哭俨然一匹小兽
后来她来到这座城市在这座城市遇见我
那是夏天我们没有说话却默默相爱了
她并不知道我的身世也没问过我的身世
只是我们相爱了就难解难分象藤蔓
缠绕在一起第二年她怀上了孩子
我们只好去医院医生咔嚓两下就完了
他们漠然注视着我们小声议论着什么
把我们的宝贝放进液体那蚕豆大的宝贝还未发芽
她从手术台上下来我们抱在一起痛哭
我们还都是孩子这样的事情不能不让我们伤心
五月份我们结了婚天气很好
广场上有许多鸽子我们在一僻静处找了一间房子
我们拉上窗帘室内没有什么摆设
我默默地坐在床上女人坐在我的身边
我想说点什么我想起来该谈谈我的身世
可她说她对这一切不感兴趣
只是希望我们安安稳稳地相爱
安安稳稳地生活那天下午
有好长一段时间我们沉默不语
她抱着房东太太的那只黑猫
不停地翻弄猫的一只耳朵
弄得那只猫懒洋洋地在她的漆上打呵欠
日子就这样平静地过去了
她跟我零零星星讲了许多
有关她身世的故事
而关于我的身世她却一无所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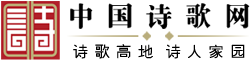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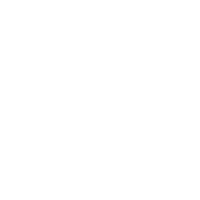

 (3次)
(3次)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34246号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34246号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