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地的栖居中忧思
——龚学敏《濒临》诗作的后人类诗学路线图
陈亚平
我在《诗与思》中说过:自然,它自己发展出了人的心灵这个可反过来判别自然和人的一个层次。因此,人是自然先决的体现者,而不是自然的先决者。人划分出的天、地、思一体的自然,只是从自然中变易出来的。
诗人作为自然灵性的唯一代言者,天职是守护自然栖身之链,反思人与自然、人与文化、人与未来——共存的后继状态。
这就是龚学敏诗集《濒临》引发的思与言。
一、动物叙事,是诗性美学的一面镜子
依我看,审美就是对事物各种关系做出诗化的直观,美学是对内心合目的感受相关的一种内心创造。诗歌演绎出的动物叙事,是人与自然在场的心灵对话与情感沟通,这种对话原型中分布的叙事脉络,带有合目的感受这一种反思之美。
因为自然与人的对话是浇灌于生命中的,生命总是有一种合目的性的生机与创造之美。诗人,能通过诗性光环的照耀,来升华自然与人之间共同依存的这一生机。诗人作为思想生命的化身,不仅有,守护生命状貌诗意母源与自然活力的神圣愿景,而且也有,还原大地栖居家园的宏大反思判断。
龚学敏《濒临》诗作演绎动物叙事的实质,不只是描绘出动物生存的危机处境与厄运环生,更是追问生命这个自为物的本原,关键是,反思了物性与人性对立之间的后自然与后人类,会带来什么样不测的未来?
我认为,一种反思,本身就会被审思的内心,更内在地改观成一种合目的性的创造性的心悦美感。生命的合目的性,在人心目中的生命诉求上,可以蕴涵生存处境沉思意义上的悲壮之美的诗意。这是动物与自然、人与环境、自然与未来……关系中所意蕴的诗意美感,是一种美学智性转向诗学知性的铸造。我们不妨读解龚学敏这段诗句:
“来吧
前世的霰弹被我开成了满身的花朵。
铁在风中疾行,村庄在我身后一点点地迷路
……
我用铁奔跑的速度划出的线,钓鱼
森林的餐桌被天空的白布裹胁”(龚学敏《金钱豹》)
诗昭告我们:人对自然的毁灭,是通过对欲望的开放来实现的。诗中一种马尾松透过光一样的语感,有一种无法变形的活力和诺日朗潮润的地心的气息,不断地在我们身边展示它的林涛声,带着幽谷中沉积的山脉气韵。句中“我开成了满身的花朵”的 “我”,是诗人把金钱豹诗意般还原成了真正的主体,让拥有智能的金钱豹处在了与人类平等的中心。金钱豹的自我,否定了人是自然大地的主人——这种优先性。诗句借助金钱豹的感知角度,从闪射着山野气的荒僻“天空的白布”中,渲染出人类的“铁”对“森林的餐桌”的毁灭。这句有象征意味的转喻表现出,兽界的厄运,衬托出了人世的生物强权,衬托出了大自然低沉的不知道未来的无形焦虑。
《金钱豹》这首诗代言自然之魂,向我们昭示出,自然通过人而改变了自然自身的命运。因为人已经把自然变成自己的奴役对象,并让自然只服从人自身的无止境凌驾。就像诗人龚学敏感知的:
“被催雨弹纷纷打成散装的云朵
已经失去乳房的圆润。榕树的记忆
匍匐在白描的连环画中,时间和童年
旧成枯瘦的笔画。”(龚学敏《西双版纳寻野象不遇》)
诗句“被催雨弹纷纷打成散装的云朵”, 把我们的思绪,从仰望得到干净星空的歌剧布景的山巅上,瞬间跳到山背后沉沉的黑暗中。“榕树的记忆/匍匐在白描的连环画中”暗喻着,仿佛远处一条闪亮的大河静静斜流的地方,有一座光秃的山岭很沉寂。这“白描的连环画”,让我们心中深处引起不敢多玩味一会儿的丢了魂的隐痛,它会伴随我们度过未来一生不测的忧思。
从我的体验看,诗人龚学敏是用生命的漂泊,在心灵的异乡中创造诗歌新的生命方向。因此,动物叙事的诗化等于是人向自然的解密,是把自然自己的心灵旅程,展示给人的心灵旅程,让人们重构心灵旅程的其他可能性。因此,动物自身降示的诗意美感,就化身在龚学敏守护自然禀赋那一灵魂净化的诗化演述中,这构成了为创造灵魂世界更加接近自然的一种思化的诗意。
对龚学敏《濒临》诗集第一辑《白鳍豚》、《乌鸦》、《海龟》、《鱼鹰》、《白狐》、《成都麻羊》、《刀鱼》、《河豚》、《雨燕》、《啄木鸟》等26首诗的读解,有一种未知的不安的思虑,在形成内心潮水涌来的漩涡中,让我仰天设想:
自然为人开启了唯一的栖身之地,但自然是有不可代替的、不可危害的神力界限的。自然的天律决不会被人的思维和意志所改变,而是在它得到的天启中,合目的性地保持它自给的运化法则。
从表现形式看,第一辑的26首诗,十分重视情节结构的多元化和主观透视出来的反讽荒诞相互结合,讲究以均称的多画面切换产生连续动感为目的。诗句在描述场景方面,采用了一种非浮华构图式的简略逼真,来达到强有力的凸显壮观倾向的渲染。有点自然印象主义的趋势。试分析典型的标志性句子结构:
1)句子用画面结构,穿插象征结构再结合到写实结构中,形成读解开放式的空间感。
“视野被近视的喷雾器越写越小
拄着时间药味的拐杖
老迈的成群的乌鸦,被打成天空的
霰弹” (龚学敏《乌鸦》)
句子的象征结构“近视的喷雾器越写越小”穿插到写实结构“成群的乌鸦”,再结合到画面结构“被打成天空的霰弹”。
2)双层隐喻跳跃式的曲折句,穿插到弥散性的隐形叙事单元的跳跃中,来构成一个多义扭结的语义环。
“一柄银刀把雾霾的皮,从江身上
剖开
让风收走。
刀给整条的江剔骨
时间游刃有余,宋时的苏轼、陆游……
是一条江最鲜的几滴水。”(龚学敏《刀鱼》)
句子“一柄银刀把雾霾的皮”有“一柄银刀”与“雾霾的皮”组成了双层隐喻结构,穿插到隐形的叙事单元“时间游刃有余”的跳跃表达式中。于是,句子能感到叙事情节时有时无的隐形环绕,让读者的想象力产生奔放的燃点。
龚学敏这类动物叙事的句法风格,算是从古典动物叙事类型和现代动物叙事类型之间的一个继承式革新。这种创造来源于对自然美学的灵魂改造,也可以透现出汉臧语系歌诗那种平行式和对比式手法的远影。比如,龚学敏从“秋天的阳光中布满了黄金的虫”单一句法结构,发展到“冰的形式主义,……在水的画布上”增殖式句法结构——这种名词链接名词的蜂巢联想性,以追求非宏大的自然心语的境界为准则。
因为自然的自我显现,是从根本上独立于人的显现而显现,独立于人的改变而改变。它自我现出所依据的尺度,也是由它自身运化提供的。人不能改变这个尺度的本身,也是由自然独自决定的。
回归自然生命中心主义的言说,是龚学敏借助诗的美感表现力,来超越脑海中那些物界和人界的人为界限的唯独追求。他的诗不是为自然而描写自然,他是为他自己灵与肉中的自然宿源,来驾驭诗的反思与批判锋锐,来讽喻人对自然的工具性观念。他隐晦而罕见的抒情叙事法,遵循了自然灵性的任意、感官的机敏、无羁、奔放的天律,让思性的说教,跳起了神奇的果卓之舞。但这种远离尘世的自然林海装饰的汉藏式诗体,还是保持了诗人用灵魂感受思想的自我在场。就像诗的思想在飞,在洛沃色溪的镜子中跳跃,把鸟的声音悬放在句子的南方。
二、动物叙事,与后现代哲学叙事相辉映
我从后现代思想方法来看,龚学敏的多元诗学策略走向,已经进入到后现代观念与现代观念的关联圈。因此,他诗歌表现出的非叙事完形化与隐喻突变地跳跃化的个性特征,无疑地,就切近了一种有建设性效果的后现代哲学叙事的有限碎片化,同时又交织着对立、扭结、变形、非逻辑性的那种超现实的光晕。本质上,龚学敏思想生命能够追溯的母源中,自然的生命就是可见的心灵思想,有风在追逐海子马匹和林荫草气的新自然主义血脉。显然,渗透他身心的,是以自然格的人化情志,来批判人格欲望的自然化现实这种后现代自然观的起因。所以,龚学敏借助动物境况演绎出的哲学性叙事,是一种变革中的哲学演述和形象的演绎,它借助故事情节一样的实体序列,让读解的感知力既朝理性的方向偏移,又保持了感性的底蕴。哲学以叙事的形式呈现,就达到了最佳状态。本质上,是龚学敏思想生命诉诸于自然生命形而上综合的一种特殊诗式。这种诗式,带有山峰一样重叠在云中的先验性的生物本能之谜,而不是模仿弗罗斯特诗歌中的生态哲学观。
在契合自然生机反思意识的后现代语境下,龚学敏的创作手法与之对应地呈现出,只偏重开放性的叙事结构;不展开故事的细节,让句子画面与画面之间产生一种朦胧式断裂,只靠想象来连接一种完整的句式走向。句群中,不断切换一些拟人化的视角,又不断编织一个隐喻连环另一个通感的跳跃网。同时,句子画面的写实与字面叙理的写意,二者始终交集在一起,形成思想与诗化之间的合目的性。 以此凸显,他对动物反思中自创出来的一种沉思的诗感。试读解诗句:
“爬在林荫小道上思想的雾,被刺猬划成
网格,猎人与马尾松在路边
不停越界,争辩气候与河流的易容术
鸟鸣测试时间的清洁度
过往的人心是准确的试纸。
工业醒来的第一天
空气和胆色粗壮成霾
成攥紧的巨大拳头,击打树叶
和它侥幸的口罩背面
每一个方向都在控制生育,时间被琐碎”(龚学敏《刺猬》)
诗句“思想的雾”,本身是隐喻思想连绵在树影之下的林中路,渴望重返被遮蔽的存在本身。但改变了“气候与河流”的“路边”的“马尾松”,被“猎人”缩小了,刺猬的身心只能受制于“划成网格”的领地。
第二辑、第三辑《刺猬、《黑颈鹤》、《岩羊》、《海鸥》、《藏羚羊》、《鸿雁》、《北极熊》、《大熊猫》等52首诗,教科书似地折射出,龚学敏生态危机意识中所秉持的批判人类中心主义、人类生物强权主义、资源利己主义至上观的生态性后现代精神。与福克纳《去吧,摩西》的生态后现代内涵、于坚的《哀滇池》、徐刚的《伐木者,醒来!》和罗伯特•马吉欧里《哲学家与动物》相比,我觉得,龚学敏借助动物叙事本身提升出来的后现代意味的哲学式叙事,力图从人类生态濒临危机的本体论上,来丰富福克纳、吉欧里关于人对自然权利欲演述的视角。重要的是,龚学敏追求从自然生命的内在本质中,揭示出一种人与自然有机同源的哲学意蕴的关联性。也就是说,龚学敏对动物的哲学思辨依据,是从人与自然的交汇,引发上升为哲学思辨层次的交融。因为,思辨地揭示自然,才真正体现出人在自然内部的完整还原,也才能体现出自然自己的先验升华。试读代表性诗句:
1)“草原再辽阔,也要给自己的心安上栏杆”。(龚学敏《斑马》)
我们眼帘中“辽阔”与“栏杆”的自然与人之间对立的画面镜像,形成的是无法回避的大与小的矛盾,但却可以圆圈般的统一结合在一起。这就在诗中反映出,一种人与自然有机同源的对立统一哲学意蕴的亲缘性。
2)“流回来的水成为时间的叛徒”(龚学敏《刺猬》)
诗句,带有赫拉克利特“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哲学箴铭那很凉的露气,在大山静夜低沉的无形呼吸声中,捕捉我们一瞬间可能在诗句里引起的各种微妙思绪。
3)“人类已经成为自己的天敌” (龚学敏《大熊猫》)
诗句用动物处境中升华出来的哲学叙事预示我们,在人类极端中心主义的处境下,人不再是自然的盟友,人只能是自然的敌人,更是让人可以自我实现的宿敌。
龚学敏的哲学叙事带有诺日朗自然神格赋予他灵魂的诗思天性,始终有风推动着山的影子,发出穿云的天地之旷音。他的诗思已经栖身在巍峨的群山之巅,带有大自然自传体的第一人称色彩。这种大自然自传体的自动诗性,体现出人类诗歌依赖的大地性,必定是自然命运的诗意归宿。
三、动物叙事,对后人类诗学的解读
面对划时代的生态危机文学思潮,我不禁要问,生态危机意识向诗歌发出的思考高度是什么?
我预言,生态危机文学首先是后人类状态历史点的一个转折性全球文学,应该聚焦于人类批判精神下的思想开启和思辨提升。
《濒临》诗作的题材范围,形成了诗的内容原动力。其主体性的创造是无限的,它的外貌则是无限的。但要包含实体性的现实内容。
试读:
“长在女人名字上的皮草,把春日和秋天
捂出象征主义遗在壁炉旁的病毒。(龚学敏《川金丝猴》)
《濒临》主体个性的深度和广度界定了对思考的能动度。主体性格是对主体的自足化规定,它成为主体世界的个性化体系。主体性格充分发展才能引起对形式的冲动。反思主体本身的心灵,是心灵自足突现的灵机、偶成的闪幻之诗。
试读:
“城市不停地繁衍
不停地给自己设置禁欲的栏杆。”(龚学敏《斑马》)
“直到人类、动物、植物被时间捆在
烹饪的同一条食物链上。”(龚学敏《啄木鸟》)
自然的意志和心灵活动的外表,总是要通过诗的形体。因为每个诗的形体中,都有一种预设好了的魔力让它自己向更意外的形式发展……,让世界通过它们的展现而接近心灵。
《濒临》诗内心宿命中的磨难,总让人的灵魂为栖居大地而伤痛,有一种在悲剧中忍受而自解的无情的深沉。龚学敏这种点缀着全球性生态文化流向的后人类文化诗学的思化色彩,可以比肩福克纳《去吧,摩西》。
——龚学敏《濒临》诗作的后人类诗学路线图
陈亚平
我在《诗与思》中说过:自然,它自己发展出了人的心灵这个可反过来判别自然和人的一个层次。因此,人是自然先决的体现者,而不是自然的先决者。人划分出的天、地、思一体的自然,只是从自然中变易出来的。
诗人作为自然灵性的唯一代言者,天职是守护自然栖身之链,反思人与自然、人与文化、人与未来——共存的后继状态。
这就是龚学敏诗集《濒临》引发的思与言。
一、动物叙事,是诗性美学的一面镜子
依我看,审美就是对事物各种关系做出诗化的直观,美学是对内心合目的感受相关的一种内心创造。诗歌演绎出的动物叙事,是人与自然在场的心灵对话与情感沟通,这种对话原型中分布的叙事脉络,带有合目的感受这一种反思之美。
因为自然与人的对话是浇灌于生命中的,生命总是有一种合目的性的生机与创造之美。诗人,能通过诗性光环的照耀,来升华自然与人之间共同依存的这一生机。诗人作为思想生命的化身,不仅有,守护生命状貌诗意母源与自然活力的神圣愿景,而且也有,还原大地栖居家园的宏大反思判断。
龚学敏《濒临》诗作演绎动物叙事的实质,不只是描绘出动物生存的危机处境与厄运环生,更是追问生命这个自为物的本原,关键是,反思了物性与人性对立之间的后自然与后人类,会带来什么样不测的未来?
我认为,一种反思,本身就会被审思的内心,更内在地改观成一种合目的性的创造性的心悦美感。生命的合目的性,在人心目中的生命诉求上,可以蕴涵生存处境沉思意义上的悲壮之美的诗意。这是动物与自然、人与环境、自然与未来……关系中所意蕴的诗意美感,是一种美学智性转向诗学知性的铸造。我们不妨读解龚学敏这段诗句:
“来吧
前世的霰弹被我开成了满身的花朵。
铁在风中疾行,村庄在我身后一点点地迷路
……
我用铁奔跑的速度划出的线,钓鱼
森林的餐桌被天空的白布裹胁”(龚学敏《金钱豹》)
诗昭告我们:人对自然的毁灭,是通过对欲望的开放来实现的。诗中一种马尾松透过光一样的语感,有一种无法变形的活力和诺日朗潮润的地心的气息,不断地在我们身边展示它的林涛声,带着幽谷中沉积的山脉气韵。句中“我开成了满身的花朵”的 “我”,是诗人把金钱豹诗意般还原成了真正的主体,让拥有智能的金钱豹处在了与人类平等的中心。金钱豹的自我,否定了人是自然大地的主人——这种优先性。诗句借助金钱豹的感知角度,从闪射着山野气的荒僻“天空的白布”中,渲染出人类的“铁”对“森林的餐桌”的毁灭。这句有象征意味的转喻表现出,兽界的厄运,衬托出了人世的生物强权,衬托出了大自然低沉的不知道未来的无形焦虑。
《金钱豹》这首诗代言自然之魂,向我们昭示出,自然通过人而改变了自然自身的命运。因为人已经把自然变成自己的奴役对象,并让自然只服从人自身的无止境凌驾。就像诗人龚学敏感知的:
“被催雨弹纷纷打成散装的云朵
已经失去乳房的圆润。榕树的记忆
匍匐在白描的连环画中,时间和童年
旧成枯瘦的笔画。”(龚学敏《西双版纳寻野象不遇》)
诗句“被催雨弹纷纷打成散装的云朵”, 把我们的思绪,从仰望得到干净星空的歌剧布景的山巅上,瞬间跳到山背后沉沉的黑暗中。“榕树的记忆/匍匐在白描的连环画中”暗喻着,仿佛远处一条闪亮的大河静静斜流的地方,有一座光秃的山岭很沉寂。这“白描的连环画”,让我们心中深处引起不敢多玩味一会儿的丢了魂的隐痛,它会伴随我们度过未来一生不测的忧思。
从我的体验看,诗人龚学敏是用生命的漂泊,在心灵的异乡中创造诗歌新的生命方向。因此,动物叙事的诗化等于是人向自然的解密,是把自然自己的心灵旅程,展示给人的心灵旅程,让人们重构心灵旅程的其他可能性。因此,动物自身降示的诗意美感,就化身在龚学敏守护自然禀赋那一灵魂净化的诗化演述中,这构成了为创造灵魂世界更加接近自然的一种思化的诗意。
对龚学敏《濒临》诗集第一辑《白鳍豚》、《乌鸦》、《海龟》、《鱼鹰》、《白狐》、《成都麻羊》、《刀鱼》、《河豚》、《雨燕》、《啄木鸟》等26首诗的读解,有一种未知的不安的思虑,在形成内心潮水涌来的漩涡中,让我仰天设想:
自然为人开启了唯一的栖身之地,但自然是有不可代替的、不可危害的神力界限的。自然的天律决不会被人的思维和意志所改变,而是在它得到的天启中,合目的性地保持它自给的运化法则。
从表现形式看,第一辑的26首诗,十分重视情节结构的多元化和主观透视出来的反讽荒诞相互结合,讲究以均称的多画面切换产生连续动感为目的。诗句在描述场景方面,采用了一种非浮华构图式的简略逼真,来达到强有力的凸显壮观倾向的渲染。有点自然印象主义的趋势。试分析典型的标志性句子结构:
1)句子用画面结构,穿插象征结构再结合到写实结构中,形成读解开放式的空间感。
“视野被近视的喷雾器越写越小
拄着时间药味的拐杖
老迈的成群的乌鸦,被打成天空的
霰弹” (龚学敏《乌鸦》)
句子的象征结构“近视的喷雾器越写越小”穿插到写实结构“成群的乌鸦”,再结合到画面结构“被打成天空的霰弹”。
2)双层隐喻跳跃式的曲折句,穿插到弥散性的隐形叙事单元的跳跃中,来构成一个多义扭结的语义环。
“一柄银刀把雾霾的皮,从江身上
剖开
让风收走。
刀给整条的江剔骨
时间游刃有余,宋时的苏轼、陆游……
是一条江最鲜的几滴水。”(龚学敏《刀鱼》)
句子“一柄银刀把雾霾的皮”有“一柄银刀”与“雾霾的皮”组成了双层隐喻结构,穿插到隐形的叙事单元“时间游刃有余”的跳跃表达式中。于是,句子能感到叙事情节时有时无的隐形环绕,让读者的想象力产生奔放的燃点。
龚学敏这类动物叙事的句法风格,算是从古典动物叙事类型和现代动物叙事类型之间的一个继承式革新。这种创造来源于对自然美学的灵魂改造,也可以透现出汉臧语系歌诗那种平行式和对比式手法的远影。比如,龚学敏从“秋天的阳光中布满了黄金的虫”单一句法结构,发展到“冰的形式主义,……在水的画布上”增殖式句法结构——这种名词链接名词的蜂巢联想性,以追求非宏大的自然心语的境界为准则。
因为自然的自我显现,是从根本上独立于人的显现而显现,独立于人的改变而改变。它自我现出所依据的尺度,也是由它自身运化提供的。人不能改变这个尺度的本身,也是由自然独自决定的。
回归自然生命中心主义的言说,是龚学敏借助诗的美感表现力,来超越脑海中那些物界和人界的人为界限的唯独追求。他的诗不是为自然而描写自然,他是为他自己灵与肉中的自然宿源,来驾驭诗的反思与批判锋锐,来讽喻人对自然的工具性观念。他隐晦而罕见的抒情叙事法,遵循了自然灵性的任意、感官的机敏、无羁、奔放的天律,让思性的说教,跳起了神奇的果卓之舞。但这种远离尘世的自然林海装饰的汉藏式诗体,还是保持了诗人用灵魂感受思想的自我在场。就像诗的思想在飞,在洛沃色溪的镜子中跳跃,把鸟的声音悬放在句子的南方。
二、动物叙事,与后现代哲学叙事相辉映
我从后现代思想方法来看,龚学敏的多元诗学策略走向,已经进入到后现代观念与现代观念的关联圈。因此,他诗歌表现出的非叙事完形化与隐喻突变地跳跃化的个性特征,无疑地,就切近了一种有建设性效果的后现代哲学叙事的有限碎片化,同时又交织着对立、扭结、变形、非逻辑性的那种超现实的光晕。本质上,龚学敏思想生命能够追溯的母源中,自然的生命就是可见的心灵思想,有风在追逐海子马匹和林荫草气的新自然主义血脉。显然,渗透他身心的,是以自然格的人化情志,来批判人格欲望的自然化现实这种后现代自然观的起因。所以,龚学敏借助动物境况演绎出的哲学性叙事,是一种变革中的哲学演述和形象的演绎,它借助故事情节一样的实体序列,让读解的感知力既朝理性的方向偏移,又保持了感性的底蕴。哲学以叙事的形式呈现,就达到了最佳状态。本质上,是龚学敏思想生命诉诸于自然生命形而上综合的一种特殊诗式。这种诗式,带有山峰一样重叠在云中的先验性的生物本能之谜,而不是模仿弗罗斯特诗歌中的生态哲学观。
在契合自然生机反思意识的后现代语境下,龚学敏的创作手法与之对应地呈现出,只偏重开放性的叙事结构;不展开故事的细节,让句子画面与画面之间产生一种朦胧式断裂,只靠想象来连接一种完整的句式走向。句群中,不断切换一些拟人化的视角,又不断编织一个隐喻连环另一个通感的跳跃网。同时,句子画面的写实与字面叙理的写意,二者始终交集在一起,形成思想与诗化之间的合目的性。 以此凸显,他对动物反思中自创出来的一种沉思的诗感。试读解诗句:
“爬在林荫小道上思想的雾,被刺猬划成
网格,猎人与马尾松在路边
不停越界,争辩气候与河流的易容术
鸟鸣测试时间的清洁度
过往的人心是准确的试纸。
工业醒来的第一天
空气和胆色粗壮成霾
成攥紧的巨大拳头,击打树叶
和它侥幸的口罩背面
每一个方向都在控制生育,时间被琐碎”(龚学敏《刺猬》)
诗句“思想的雾”,本身是隐喻思想连绵在树影之下的林中路,渴望重返被遮蔽的存在本身。但改变了“气候与河流”的“路边”的“马尾松”,被“猎人”缩小了,刺猬的身心只能受制于“划成网格”的领地。
第二辑、第三辑《刺猬、《黑颈鹤》、《岩羊》、《海鸥》、《藏羚羊》、《鸿雁》、《北极熊》、《大熊猫》等52首诗,教科书似地折射出,龚学敏生态危机意识中所秉持的批判人类中心主义、人类生物强权主义、资源利己主义至上观的生态性后现代精神。与福克纳《去吧,摩西》的生态后现代内涵、于坚的《哀滇池》、徐刚的《伐木者,醒来!》和罗伯特•马吉欧里《哲学家与动物》相比,我觉得,龚学敏借助动物叙事本身提升出来的后现代意味的哲学式叙事,力图从人类生态濒临危机的本体论上,来丰富福克纳、吉欧里关于人对自然权利欲演述的视角。重要的是,龚学敏追求从自然生命的内在本质中,揭示出一种人与自然有机同源的哲学意蕴的关联性。也就是说,龚学敏对动物的哲学思辨依据,是从人与自然的交汇,引发上升为哲学思辨层次的交融。因为,思辨地揭示自然,才真正体现出人在自然内部的完整还原,也才能体现出自然自己的先验升华。试读代表性诗句:
1)“草原再辽阔,也要给自己的心安上栏杆”。(龚学敏《斑马》)
我们眼帘中“辽阔”与“栏杆”的自然与人之间对立的画面镜像,形成的是无法回避的大与小的矛盾,但却可以圆圈般的统一结合在一起。这就在诗中反映出,一种人与自然有机同源的对立统一哲学意蕴的亲缘性。
2)“流回来的水成为时间的叛徒”(龚学敏《刺猬》)
诗句,带有赫拉克利特“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哲学箴铭那很凉的露气,在大山静夜低沉的无形呼吸声中,捕捉我们一瞬间可能在诗句里引起的各种微妙思绪。
3)“人类已经成为自己的天敌” (龚学敏《大熊猫》)
诗句用动物处境中升华出来的哲学叙事预示我们,在人类极端中心主义的处境下,人不再是自然的盟友,人只能是自然的敌人,更是让人可以自我实现的宿敌。
龚学敏的哲学叙事带有诺日朗自然神格赋予他灵魂的诗思天性,始终有风推动着山的影子,发出穿云的天地之旷音。他的诗思已经栖身在巍峨的群山之巅,带有大自然自传体的第一人称色彩。这种大自然自传体的自动诗性,体现出人类诗歌依赖的大地性,必定是自然命运的诗意归宿。
三、动物叙事,对后人类诗学的解读
面对划时代的生态危机文学思潮,我不禁要问,生态危机意识向诗歌发出的思考高度是什么?
我预言,生态危机文学首先是后人类状态历史点的一个转折性全球文学,应该聚焦于人类批判精神下的思想开启和思辨提升。
《濒临》诗作的题材范围,形成了诗的内容原动力。其主体性的创造是无限的,它的外貌则是无限的。但要包含实体性的现实内容。
试读:
“长在女人名字上的皮草,把春日和秋天
捂出象征主义遗在壁炉旁的病毒。(龚学敏《川金丝猴》)
《濒临》主体个性的深度和广度界定了对思考的能动度。主体性格是对主体的自足化规定,它成为主体世界的个性化体系。主体性格充分发展才能引起对形式的冲动。反思主体本身的心灵,是心灵自足突现的灵机、偶成的闪幻之诗。
试读:
“城市不停地繁衍
不停地给自己设置禁欲的栏杆。”(龚学敏《斑马》)
“直到人类、动物、植物被时间捆在
烹饪的同一条食物链上。”(龚学敏《啄木鸟》)
自然的意志和心灵活动的外表,总是要通过诗的形体。因为每个诗的形体中,都有一种预设好了的魔力让它自己向更意外的形式发展……,让世界通过它们的展现而接近心灵。
《濒临》诗内心宿命中的磨难,总让人的灵魂为栖居大地而伤痛,有一种在悲剧中忍受而自解的无情的深沉。龚学敏这种点缀着全球性生态文化流向的后人类文化诗学的思化色彩,可以比肩福克纳《去吧,摩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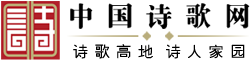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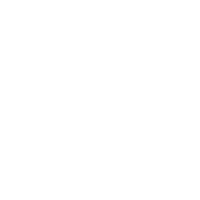

 (3次)
(3次)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34246号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34246号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