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摘要:矢野彻是公认的日本科幻元老,其小说《密友》中的机器人具有海洋打捞的功能,同时是富有人性的科技产物,代表着人们最初寄予人工智能的期望与要求,也暴露了科技与伦理关系的早期隐患;石黑一雄作为日裔英籍作家,在创作时除了更具世界情怀以外,小说《别让我走》还将对科技未来的迷茫与海洋情节联系在一起。从《密友》到《别让我走》,不仅可以看到科幻创作的时代跟进,两位作者海洋情怀的对比也为阅读现代科技伦理提供了更为独到的视角。
关键词:矢野彻;石黑一雄;科技伦理;海洋情怀
从矢野彻到石黑一雄:论科幻文学中的海洋情怀
——以《密友》和《别让我走》为例
飞速发展的科技迅速覆盖了人们的日常,带来便捷高效生活的同时,也引发了科技与伦理的长期论战。文学一直试图通过幻想的方式走在科技之前,无数文学家对未来社会做过预言并写成科幻小说。其中,东方籍作家对科幻小说写作的参与,不仅表达了自己的科技伦理立场,也是其世界情怀的体现,日本的矢野彻和石黑一雄便是如此。
矢野彻是公认的日本科幻元老,其小说《密友》中的机器人具有着海洋打捞的功能,同时是富有人性的科技产物,代表着人们最初寄予人工智能的期望与要求,也暴露了科技与伦理关系的早期隐患;石黑一雄作为日裔英籍作家,在创作时除了更具世界情怀以外,还将对科技未来的迷茫与海洋情节联系在一起,小说《别让我走》将对生物工程技术的不信任与理性思索描写到极致。从《密友》到《别让我走》,不仅可以看到科技的时代跟进,两位作者海洋情怀的对比也为阅读现代科技伦理提供了更为独到的视角。
截止到2018年8月,知网检索可以发现,国内学界对日本科幻小说本身的研究并不多,且大多都从民族振兴的角度切入,例如吴岩《民族振兴与国力赶超——浅析后发达国家科幻小说中的意识形态》,王占一《<日本沉没>中的“灾难文化”——日本人的危机意识解读》等。而对石黑一雄的科幻伦理小说《别让我走》的研究集中在了存在主义、文学伦理、反乌托邦色彩等几个方面;对矢野彻《密友》的研究暂无。通过对比发现,《密友》与《别让我走》中都有着对“海洋”的关注,海洋意象的植入不仅是情节发展的一部分,还与作家对科技伦理的思考发生着联系。
一、《密友》:在海洋童话中阅读现实
海洋是孕育童话的摇篮。国外的安徒生童话《海的女儿》、马克·吐温《汤姆·索亚历险记》等故事中都有着深刻的海洋情节,我国深受儿童喜爱的神话故事《西游记》、《哪吒闹海》等中也有着鲜明的海洋主题。上世纪末,矢野彻的《密友》亦是作为儿童读本和其他日本童话一起进入国内文学市场,从而开启了中日儿童文学交流的大门。然而《密友》作为矢野彻对科幻小说的探索,意义不仅限于童话,在对涉及科技伦理的小说阅读上,其为我们提供了从童话到科幻现实的过度和脱离。
日本的科幻小说从翻译起步。矢野彻是公认的日本科幻元老,在20世纪初通过大量翻译西方的科幻小说,开拓了日本科幻的天空。除此之外,他还主动进行小说创作,其中短篇小说《密友》讲述了日本一名流浪青年与一个被遗弃的机器人相遇后一起生活的故事。
整部小说的人物只有两个,帮助解决物质困难的机器人,赋予机器人人性的青年,两者关系看起来十分和谐。落魄的流浪青年在一所破屋前发现了被遗弃的机器人,于是两个人开始了在海边的生活。机器人会说话,并且掌握许多知识,他教授青年学习英语,并且在青年饥饿贫穷的时候帮助他——下海打捞沉在海底的金器去卖钱。最开始机器人并不懂得在这个世界上“应该做的事情”与“能做的事情”的区别,当青年说想吃东西时,机器人想要去偷,去抢,直到青年告诉他这样做是不对的,会被警察抓去。可见机器人并不懂在这个世界生存的法则,不过这并不妨碍他与人类一样有着感情。他喜欢青年给他讲桃太郎的童话故事,在青年提及母亲去世时,他用坚硬的大手给予安慰,甚至调侃青年去将心爱的姑娘带回来给他看。最后结尾处,在青年车祸去世后的许多年,机器人仍然守候在他们的海边小屋前,端坐在那里,就像他们第一次见面那样,不时发出嘶哑的声音,“我不会哭,但是我能发出哭的声音。朋友,你就当我在为你哭吧。”整篇小说采用对话形式,语言通俗感人。
科幻与童话的区别在于前者代表了对未来的预测,是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实现的现实。矢野彻是出生在上世纪初的作家,而他在《密友》的开头,预言的是“这是一个21世纪的大城市。朦胧的远方隐隐约约露出高耸入云的大厦和高速公路。在远离城市的郊外,残留着一些早已被人们忘却了的简陋棚屋。”这在如今看来,十分贴近现实。另外,小说中的机器人是被上一任主人“遗弃”的,青年本身对机器人的存在并不惊奇,据此推测这是一个机器人大规模服务于人类的时代,小说里机器人的功能大致可以归纳为:下海打捞、知识教育、陪伴娱乐等,这些在现在也已经得到了实现:水下打捞机器人的出现,电子词典、以及手机拓展的siri功能等。
《密友》写作之时,日本还算不上一个彻底的工业国家,封建残余并未完全肃清,资本积累方式也与西方国家还存在着一定距离,但矢野彻的创作却已经具有了同西方科幻作家一样的伦理忧患意识,看到了科技发展的背后存在的社会矛盾与伦理矛盾,其中“海洋”意象的寓意可以作以阐释。
首先,机器人和青年居住在海边的郊外,海洋隐喻着远离城市的“原始”空间。有大量文学作品可以举例,当现代人的精神陷入颓废迷惘时,习惯于从原始空间中寻求安慰,像是艾·略特《荒原》中的圣杯传说、毛姆《月亮与六便士》中的原始神话等等,都是如此。这固然使人想到心理学家荣格所提出的“集体无意识”,认为这其中也许是同一个“原型”在起作用。但究其现实原因,可以参照美国比较文学学者马泰·卡内林斯库的著作《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中的说法,认为是“审美现代性”与“世俗现代性”的对立——审美现代性是以人为核心,主张用审美感性去对抗技术理性,是现代化进程的反抗力量,世俗现代性则相反。《密友》中的青年显然是站在时代发展末流的人,通过机器人与“海洋”发生联系,机器人对他的帮助和救赎,其实也就是海洋对他的关怀和救赎。
而从生态主义立场上来看,海洋承担的自然资源角色也暴露了社会和人性的贪婪与堕落。海洋提供了青年的生活来源,在不触碰法律、不偷不抢又不想劳动的情况下,他只能靠机器人一次次下海打捞来赚钱,从这个角度,海洋是掠夺的对象,机器人是人类的同谋。此外,机器人作为人工智能,替代了人们的日常劳动,人的劳动意义便被缩减,失业者增加,整个社会的待业人群上升,于是有了流浪的青年,而机器人之所以被矢野彻赋予人类的外形,而不是像一台机器、手机那样,在于其有了人性、人的感情,这也是整个故事最动人的一部分。不过,作为机器人自身,他的对话内容永远在强调自己只是个“佣人”,“机器人私自藏钱是不应该的”,这种关系是从属的,不对等的,这与海洋给予人类慰藉,而人类只懂得掠夺甚至破坏,关系的本质是一样的。这是《密友》中值得进一步反思的问题。
二、《别让我走》:克隆人的宿命与缄默的海洋
如果说机器人尚不能以人性的角度对待之,那么克隆人的话题便使问题变得深刻而复杂起来。在当今社会,生物工程是热门话题,克隆人也成为科幻小说的重要题材。石黑一雄出生在上世纪中期的日本长崎,后移居英国,1983年开始发表小说,主要作品有《群山淡景》、《浮世画家》和《长日将尽》等。曾获得1989年布克奖、大英帝国勋章、法国艺术及文学骑士勋章等多个奖项。《别让我走》蕴含了作家石黑一雄以往创作中未曾涉及的科幻未来色彩。小说中克隆人凯茜作为叙事者追溯了自己过去的生活经历以及与好友汤米、露丝之间发生的故事。他们在寄宿学校“黑尔舍姆”一起长大、接受教育,与平常人一样体味嫉妒和猜忌、拥有梦想和感情,却始终无法逃脱为人类捐献身体器官、最终走向死亡的悲惨宿命。
小说中有一个根本不存在的“推迟捐献”的传说,多数克隆人以这个传说为信仰,艰难而勇敢地活着。黑尔舍姆学校将一部分克隆人保护起来,教育他们,使他们获得知识和艺术的熏陶,努力使他们成为有思想的人,与其他坐以待毙、麻木等死的克隆人区别开来,并且积极鼓励这部分克隆人进行艺术创作,因为“美术作品会展现他们的灵魂”。传说中,如果两个人足够相爱、且能够以自己的画打动“夫人”的话,便可以“推迟捐献”,从而获得和朋友爱人相处的时间。
凯茜和汤米每次寻找这位夫人的时候,便会有关于海洋的描写,由绫乃遥主要的日剧《别让我走》中也特意强调了这个镜头。最初,克隆人被禁闭在“黑尔舍姆”,看不到外面的世界,看不到大海,而他们长大成人,可以走出学校、住在各自的社区等待自己为人类捐献器官的命运时,凯茜和汤米等人看到了缤纷的人群,看到了大海。汤米等人以为走出学校就获得了自由,像大海一样,但他们看到的是海岸的礁石上挂满了垃圾、塑料袋,周边空无一人,只有毫无生气的海浪声。汤米和凯茜苦苦寻找,等找到那位夫人时却得知“推迟捐献”的传说根本不存在,这时汤米将自己心爱的足球踢向了海洋,与海面上漂浮的垃圾混为一起,一如汤米崩溃的将死之心。汤米最后一次捐献后终于走向了死亡,凯茜伤心过度,来到海边想要结束自己惨淡的生命时,那只足球又从海上飘到了她面前,搁浅在礁石边。
很多研究者认为小说中克隆人的惨状无疑影射了人类社会中处于边缘地位的弱势群体所面临的生存困境。但是作者关注的焦点虽然是人类的普世性生存体验,但很明显,整部小说对克隆人是否为“人”的争议一直存在,甚至可以说,文本中默认的社会环境是,他们如“牲畜一般存在着”,人们“宁可相信这些器官是无中生有而来的或者最多也就是相信他们是在什么真空里培育出来的”。所以,本文认为,这部小说中的克隆人并不能作为人类的“弱势群体”来研究,一方面弱势群体是指贫困者或者残疾人,克隆人身体健康而且智力水平并不低下;另一方面,克隆人本身身份并不明确,一旦将其确定为“人”,那么就与我们一直倡导的人权相悖。因此,笔者认为石黑一雄更多是在号召人们正视自己正在致力于研究的科技成果的伦理后果。
科幻小说带给人们的震撼效果在于其模拟出了无与伦比的真实性,用这种真实性使人们进入到作者模拟好的环境,从而引起共鸣和反思。首先,石黑一雄的主人公用“学生”来替代“克隆人”这个字眼,意在忽略他们的特殊性,如评论家注意到的,这部小说和一般科幻小说不同,石黑一雄的小说中没有对克隆技术的描写,这就进一步淡化了小说人物的特殊性,缩小了与读者之间的距离。其次,石黑一雄选取了三位个性明显的克隆人,从他们的视角来展现克隆人的生活和心理活动,和普通人一样,他们经历了从童年到青少年再到成年的成长过程,和过程中发生的学生之间的嘲笑、朦胧的爱情、昔日好友插足三角恋、异性关系、爱情、离别与重逢以及三人之间真正的友谊,作者刻画的细节很真实,细品之后不难发现,文中的情节都是现实社会的翻版。这种掺杂着现实的刻画,进一步让我们思考克隆人作为正常人去拥有一个普通人生的可能性,虽然这种愿望很卑微,却无比艰难,于是我们在发展科技的路上,思及的伦理问题也就更加复杂。
文本中,凯茜看到海面上漂浮过来的足球,放弃了自杀的念头,我们可能会认为,凯茜是联想到了她与汤米为了活着所做的一系列努力,足球寄托着汤米的期望与不舍,她要代替汤米继续辛苦地活着而不能简单地结束自己。但凯茜驾车离开的同时,也等于远离了她与汤米一起呼喊过的海洋,这是否是放弃了曾经的坚持、麻木地走向克隆人的命运呢?人类为了自己的私利,创造出克隆人来解决目前医学无法解决的疾病,并以器官替换来维持,这也是克隆人唯一的生命意义,而克隆人不停捐献出自己的器官,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如同守卫和平的战士,我们该称赞、还是该忏悔呢?海洋是缄默的。
三、从《密友》到《别让我走》:在“海水”的多层折射下阅读现代科技伦理
《密友》和《别让我走》的篇幅、论述风格、写作技巧等都不相同,但“海洋”意象的植入却让我们发现两者的创作内核有着奇妙的联系和一致性。从《密友》到《别让我走》,为我们在接触同类科幻题材的小说时,提供了多层面的阅读方式,如同海水折射下出现的重重幻景。
首先,人类征服的欲望无处不在,人们总是一边歌颂,一边反思。例如,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塑造了一个和大海、鲨鱼搏斗的硬汉形象,他宁可被毁灭也不可被征服的精神是英雄主义和自强不息精神的凝缩,同时,批评家也关注到了其中蕴含的丛林法则和生存竞争的伦理意识,更加倡导和谐的自然观念。从这个角度出发,人类是生存竞争的胜利者,发明科技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人类生活,机器人和生物工程的的初衷就是如此。哪怕机器人有了人脑功能的,他们思考的出发点仍是如何让人类生活地更舒适,用《密友》中的话就是“机器人是有义务帮助人类的”;克隆人的出现是为了解决人类无法克服的疾病难题,为人类提供器官移植。
然而,地球上存在着不同的生物圈,从而也就存在着不同的伦理圈,人类的生存发展不能伦理越位,不能无限度地入侵其他生物的伦理领域,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英国科幻小说家H·G威尔斯的《莫罗博士的岛》就展现了一个人类与动物之间伦理混乱的世界,令人陷入深刻的反省。而人与人工智能之间关系的思考、人与克隆人之间的伦理难题同样复杂,微博上有人模拟人脑的世界做出图片,显示人的大脑像宇宙一样浩渺无边,而先进机器人大脑的制造,不再是模仿人脑的学习功能,而是再现人脑的工作原理,这就使得机器人脑在运转过程中会变得越来越聪明,与人脑一样用自己的思维方式去思考问题,《密友》中的机器人就是这种类型,我们就算无法将机器人看作是一类“生物”,也无法忽略其“人格”属性,并且,这类属性与人类之间的“忠仆”关系是否真的像书中描述的那样平衡可靠、不会背叛人类?《别让我走》克隆人生存状态就更加触目惊心了,克隆人的使命就是为人类提供器官捐献,直到死亡,哪怕有克隆人在公众场所采取自杀的方式反抗,依旧激不起人们习以为常的冷漠,直到有一天,当医生问一个老人需不需要克隆人的器官时,老人十分恍惚:我都这么老了,可是他们还年轻……可见,科技虽然始终都为人类服务,但是伦理是不可罔顾的。
因此,我们必须承认的是人类的认识是有限的,暂时无法平衡经济发展中一些伦理关系——如当下最显著的追求商业利润与环境恶化之间的关系。大量的科幻小说、科幻电影都将结局回归于“永恒博爱”的世界愿望主题,无论是星球大战还是汽车人变身,人类所有的初衷仿佛都在于拥有一个和平充满爱的世界。《密友》里青年与机器人之间也存在着相互尊重,青年没有想过完全地占有和统治机器人,因为他知道机器人是有思想和感情的;机器人也仅限于帮助青年有一个平凡安定的生活,而不是无限制地满足人类的贪婪。《别让我走》中黑尔舍姆学校对克隆人的艺术教育、“延迟捐献”的美好传说,虽然充满了讽刺和悲情意味,但正是这种渺小而执着的夙愿,让他们在面对麻木冷漠的捐献与死亡时,依然心存美好。这些如同浮士德无限探索后的填海救赎,虽然是茫茫宇宙中的小小星辰,却让人叹息之余又感动着。
所以两则故事的结尾冷静而又充盈着些许温度:
“冬去春来,年复一年。机器人还是坐在原来的地方,发出哭泣的声音。渐渐地,机器人身上长出了锈,发声的部位也开始生锈了。有一天,哭声终于停止了。现在,机器人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坐在小屋边。”
——矢野彻《密友》
“我只等了一会儿,然后钻进车里,驶向我应该待的地方。”
——石黑一雄《别让我走》
——以《密友》和《别让我走》为例
飞速发展的科技迅速覆盖了人们的日常,带来便捷高效生活的同时,也引发了科技与伦理的长期论战。文学一直试图通过幻想的方式走在科技之前,无数文学家对未来社会做过预言并写成科幻小说。其中,东方籍作家对科幻小说写作的参与,不仅表达了自己的科技伦理立场,也是其世界情怀的体现,日本的矢野彻和石黑一雄便是如此。
矢野彻是公认的日本科幻元老,其小说《密友》中的机器人具有着海洋打捞的功能,同时是富有人性的科技产物,代表着人们最初寄予人工智能的期望与要求,也暴露了科技与伦理关系的早期隐患;石黑一雄作为日裔英籍作家,在创作时除了更具世界情怀以外,还将对科技未来的迷茫与海洋情节联系在一起,小说《别让我走》将对生物工程技术的不信任与理性思索描写到极致。从《密友》到《别让我走》,不仅可以看到科技的时代跟进,两位作者海洋情怀的对比也为阅读现代科技伦理提供了更为独到的视角。
截止到2018年8月,知网检索可以发现,国内学界对日本科幻小说本身的研究并不多,且大多都从民族振兴的角度切入,例如吴岩《民族振兴与国力赶超——浅析后发达国家科幻小说中的意识形态》,王占一《<日本沉没>中的“灾难文化”——日本人的危机意识解读》等。而对石黑一雄的科幻伦理小说《别让我走》的研究集中在了存在主义、文学伦理、反乌托邦色彩等几个方面;对矢野彻《密友》的研究暂无。通过对比发现,《密友》与《别让我走》中都有着对“海洋”的关注,海洋意象的植入不仅是情节发展的一部分,还与作家对科技伦理的思考发生着联系。
一、《密友》:在海洋童话中阅读现实
海洋是孕育童话的摇篮。国外的安徒生童话《海的女儿》、马克·吐温《汤姆·索亚历险记》等故事中都有着深刻的海洋情节,我国深受儿童喜爱的神话故事《西游记》、《哪吒闹海》等中也有着鲜明的海洋主题。上世纪末,矢野彻的《密友》亦是作为儿童读本和其他日本童话一起进入国内文学市场,从而开启了中日儿童文学交流的大门。然而《密友》作为矢野彻对科幻小说的探索,意义不仅限于童话,在对涉及科技伦理的小说阅读上,其为我们提供了从童话到科幻现实的过度和脱离。
日本的科幻小说从翻译起步。矢野彻是公认的日本科幻元老,在20世纪初通过大量翻译西方的科幻小说,开拓了日本科幻的天空。除此之外,他还主动进行小说创作,其中短篇小说《密友》讲述了日本一名流浪青年与一个被遗弃的机器人相遇后一起生活的故事。
整部小说的人物只有两个,帮助解决物质困难的机器人,赋予机器人人性的青年,两者关系看起来十分和谐。落魄的流浪青年在一所破屋前发现了被遗弃的机器人,于是两个人开始了在海边的生活。机器人会说话,并且掌握许多知识,他教授青年学习英语,并且在青年饥饿贫穷的时候帮助他——下海打捞沉在海底的金器去卖钱。最开始机器人并不懂得在这个世界上“应该做的事情”与“能做的事情”的区别,当青年说想吃东西时,机器人想要去偷,去抢,直到青年告诉他这样做是不对的,会被警察抓去。可见机器人并不懂在这个世界生存的法则,不过这并不妨碍他与人类一样有着感情。他喜欢青年给他讲桃太郎的童话故事,在青年提及母亲去世时,他用坚硬的大手给予安慰,甚至调侃青年去将心爱的姑娘带回来给他看。最后结尾处,在青年车祸去世后的许多年,机器人仍然守候在他们的海边小屋前,端坐在那里,就像他们第一次见面那样,不时发出嘶哑的声音,“我不会哭,但是我能发出哭的声音。朋友,你就当我在为你哭吧。”整篇小说采用对话形式,语言通俗感人。
科幻与童话的区别在于前者代表了对未来的预测,是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实现的现实。矢野彻是出生在上世纪初的作家,而他在《密友》的开头,预言的是“这是一个21世纪的大城市。朦胧的远方隐隐约约露出高耸入云的大厦和高速公路。在远离城市的郊外,残留着一些早已被人们忘却了的简陋棚屋。”这在如今看来,十分贴近现实。另外,小说中的机器人是被上一任主人“遗弃”的,青年本身对机器人的存在并不惊奇,据此推测这是一个机器人大规模服务于人类的时代,小说里机器人的功能大致可以归纳为:下海打捞、知识教育、陪伴娱乐等,这些在现在也已经得到了实现:水下打捞机器人的出现,电子词典、以及手机拓展的siri功能等。
《密友》写作之时,日本还算不上一个彻底的工业国家,封建残余并未完全肃清,资本积累方式也与西方国家还存在着一定距离,但矢野彻的创作却已经具有了同西方科幻作家一样的伦理忧患意识,看到了科技发展的背后存在的社会矛盾与伦理矛盾,其中“海洋”意象的寓意可以作以阐释。
首先,机器人和青年居住在海边的郊外,海洋隐喻着远离城市的“原始”空间。有大量文学作品可以举例,当现代人的精神陷入颓废迷惘时,习惯于从原始空间中寻求安慰,像是艾·略特《荒原》中的圣杯传说、毛姆《月亮与六便士》中的原始神话等等,都是如此。这固然使人想到心理学家荣格所提出的“集体无意识”,认为这其中也许是同一个“原型”在起作用。但究其现实原因,可以参照美国比较文学学者马泰·卡内林斯库的著作《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中的说法,认为是“审美现代性”与“世俗现代性”的对立——审美现代性是以人为核心,主张用审美感性去对抗技术理性,是现代化进程的反抗力量,世俗现代性则相反。《密友》中的青年显然是站在时代发展末流的人,通过机器人与“海洋”发生联系,机器人对他的帮助和救赎,其实也就是海洋对他的关怀和救赎。
而从生态主义立场上来看,海洋承担的自然资源角色也暴露了社会和人性的贪婪与堕落。海洋提供了青年的生活来源,在不触碰法律、不偷不抢又不想劳动的情况下,他只能靠机器人一次次下海打捞来赚钱,从这个角度,海洋是掠夺的对象,机器人是人类的同谋。此外,机器人作为人工智能,替代了人们的日常劳动,人的劳动意义便被缩减,失业者增加,整个社会的待业人群上升,于是有了流浪的青年,而机器人之所以被矢野彻赋予人类的外形,而不是像一台机器、手机那样,在于其有了人性、人的感情,这也是整个故事最动人的一部分。不过,作为机器人自身,他的对话内容永远在强调自己只是个“佣人”,“机器人私自藏钱是不应该的”,这种关系是从属的,不对等的,这与海洋给予人类慰藉,而人类只懂得掠夺甚至破坏,关系的本质是一样的。这是《密友》中值得进一步反思的问题。
二、《别让我走》:克隆人的宿命与缄默的海洋
如果说机器人尚不能以人性的角度对待之,那么克隆人的话题便使问题变得深刻而复杂起来。在当今社会,生物工程是热门话题,克隆人也成为科幻小说的重要题材。石黑一雄出生在上世纪中期的日本长崎,后移居英国,1983年开始发表小说,主要作品有《群山淡景》、《浮世画家》和《长日将尽》等。曾获得1989年布克奖、大英帝国勋章、法国艺术及文学骑士勋章等多个奖项。《别让我走》蕴含了作家石黑一雄以往创作中未曾涉及的科幻未来色彩。小说中克隆人凯茜作为叙事者追溯了自己过去的生活经历以及与好友汤米、露丝之间发生的故事。他们在寄宿学校“黑尔舍姆”一起长大、接受教育,与平常人一样体味嫉妒和猜忌、拥有梦想和感情,却始终无法逃脱为人类捐献身体器官、最终走向死亡的悲惨宿命。
小说中有一个根本不存在的“推迟捐献”的传说,多数克隆人以这个传说为信仰,艰难而勇敢地活着。黑尔舍姆学校将一部分克隆人保护起来,教育他们,使他们获得知识和艺术的熏陶,努力使他们成为有思想的人,与其他坐以待毙、麻木等死的克隆人区别开来,并且积极鼓励这部分克隆人进行艺术创作,因为“美术作品会展现他们的灵魂”。传说中,如果两个人足够相爱、且能够以自己的画打动“夫人”的话,便可以“推迟捐献”,从而获得和朋友爱人相处的时间。
凯茜和汤米每次寻找这位夫人的时候,便会有关于海洋的描写,由绫乃遥主要的日剧《别让我走》中也特意强调了这个镜头。最初,克隆人被禁闭在“黑尔舍姆”,看不到外面的世界,看不到大海,而他们长大成人,可以走出学校、住在各自的社区等待自己为人类捐献器官的命运时,凯茜和汤米等人看到了缤纷的人群,看到了大海。汤米等人以为走出学校就获得了自由,像大海一样,但他们看到的是海岸的礁石上挂满了垃圾、塑料袋,周边空无一人,只有毫无生气的海浪声。汤米和凯茜苦苦寻找,等找到那位夫人时却得知“推迟捐献”的传说根本不存在,这时汤米将自己心爱的足球踢向了海洋,与海面上漂浮的垃圾混为一起,一如汤米崩溃的将死之心。汤米最后一次捐献后终于走向了死亡,凯茜伤心过度,来到海边想要结束自己惨淡的生命时,那只足球又从海上飘到了她面前,搁浅在礁石边。
很多研究者认为小说中克隆人的惨状无疑影射了人类社会中处于边缘地位的弱势群体所面临的生存困境。但是作者关注的焦点虽然是人类的普世性生存体验,但很明显,整部小说对克隆人是否为“人”的争议一直存在,甚至可以说,文本中默认的社会环境是,他们如“牲畜一般存在着”,人们“宁可相信这些器官是无中生有而来的或者最多也就是相信他们是在什么真空里培育出来的”。所以,本文认为,这部小说中的克隆人并不能作为人类的“弱势群体”来研究,一方面弱势群体是指贫困者或者残疾人,克隆人身体健康而且智力水平并不低下;另一方面,克隆人本身身份并不明确,一旦将其确定为“人”,那么就与我们一直倡导的人权相悖。因此,笔者认为石黑一雄更多是在号召人们正视自己正在致力于研究的科技成果的伦理后果。
科幻小说带给人们的震撼效果在于其模拟出了无与伦比的真实性,用这种真实性使人们进入到作者模拟好的环境,从而引起共鸣和反思。首先,石黑一雄的主人公用“学生”来替代“克隆人”这个字眼,意在忽略他们的特殊性,如评论家注意到的,这部小说和一般科幻小说不同,石黑一雄的小说中没有对克隆技术的描写,这就进一步淡化了小说人物的特殊性,缩小了与读者之间的距离。其次,石黑一雄选取了三位个性明显的克隆人,从他们的视角来展现克隆人的生活和心理活动,和普通人一样,他们经历了从童年到青少年再到成年的成长过程,和过程中发生的学生之间的嘲笑、朦胧的爱情、昔日好友插足三角恋、异性关系、爱情、离别与重逢以及三人之间真正的友谊,作者刻画的细节很真实,细品之后不难发现,文中的情节都是现实社会的翻版。这种掺杂着现实的刻画,进一步让我们思考克隆人作为正常人去拥有一个普通人生的可能性,虽然这种愿望很卑微,却无比艰难,于是我们在发展科技的路上,思及的伦理问题也就更加复杂。
文本中,凯茜看到海面上漂浮过来的足球,放弃了自杀的念头,我们可能会认为,凯茜是联想到了她与汤米为了活着所做的一系列努力,足球寄托着汤米的期望与不舍,她要代替汤米继续辛苦地活着而不能简单地结束自己。但凯茜驾车离开的同时,也等于远离了她与汤米一起呼喊过的海洋,这是否是放弃了曾经的坚持、麻木地走向克隆人的命运呢?人类为了自己的私利,创造出克隆人来解决目前医学无法解决的疾病,并以器官替换来维持,这也是克隆人唯一的生命意义,而克隆人不停捐献出自己的器官,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如同守卫和平的战士,我们该称赞、还是该忏悔呢?海洋是缄默的。
三、从《密友》到《别让我走》:在“海水”的多层折射下阅读现代科技伦理
《密友》和《别让我走》的篇幅、论述风格、写作技巧等都不相同,但“海洋”意象的植入却让我们发现两者的创作内核有着奇妙的联系和一致性。从《密友》到《别让我走》,为我们在接触同类科幻题材的小说时,提供了多层面的阅读方式,如同海水折射下出现的重重幻景。
首先,人类征服的欲望无处不在,人们总是一边歌颂,一边反思。例如,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塑造了一个和大海、鲨鱼搏斗的硬汉形象,他宁可被毁灭也不可被征服的精神是英雄主义和自强不息精神的凝缩,同时,批评家也关注到了其中蕴含的丛林法则和生存竞争的伦理意识,更加倡导和谐的自然观念。从这个角度出发,人类是生存竞争的胜利者,发明科技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人类生活,机器人和生物工程的的初衷就是如此。哪怕机器人有了人脑功能的,他们思考的出发点仍是如何让人类生活地更舒适,用《密友》中的话就是“机器人是有义务帮助人类的”;克隆人的出现是为了解决人类无法克服的疾病难题,为人类提供器官移植。
然而,地球上存在着不同的生物圈,从而也就存在着不同的伦理圈,人类的生存发展不能伦理越位,不能无限度地入侵其他生物的伦理领域,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英国科幻小说家H·G威尔斯的《莫罗博士的岛》就展现了一个人类与动物之间伦理混乱的世界,令人陷入深刻的反省。而人与人工智能之间关系的思考、人与克隆人之间的伦理难题同样复杂,微博上有人模拟人脑的世界做出图片,显示人的大脑像宇宙一样浩渺无边,而先进机器人大脑的制造,不再是模仿人脑的学习功能,而是再现人脑的工作原理,这就使得机器人脑在运转过程中会变得越来越聪明,与人脑一样用自己的思维方式去思考问题,《密友》中的机器人就是这种类型,我们就算无法将机器人看作是一类“生物”,也无法忽略其“人格”属性,并且,这类属性与人类之间的“忠仆”关系是否真的像书中描述的那样平衡可靠、不会背叛人类?《别让我走》克隆人生存状态就更加触目惊心了,克隆人的使命就是为人类提供器官捐献,直到死亡,哪怕有克隆人在公众场所采取自杀的方式反抗,依旧激不起人们习以为常的冷漠,直到有一天,当医生问一个老人需不需要克隆人的器官时,老人十分恍惚:我都这么老了,可是他们还年轻……可见,科技虽然始终都为人类服务,但是伦理是不可罔顾的。
因此,我们必须承认的是人类的认识是有限的,暂时无法平衡经济发展中一些伦理关系——如当下最显著的追求商业利润与环境恶化之间的关系。大量的科幻小说、科幻电影都将结局回归于“永恒博爱”的世界愿望主题,无论是星球大战还是汽车人变身,人类所有的初衷仿佛都在于拥有一个和平充满爱的世界。《密友》里青年与机器人之间也存在着相互尊重,青年没有想过完全地占有和统治机器人,因为他知道机器人是有思想和感情的;机器人也仅限于帮助青年有一个平凡安定的生活,而不是无限制地满足人类的贪婪。《别让我走》中黑尔舍姆学校对克隆人的艺术教育、“延迟捐献”的美好传说,虽然充满了讽刺和悲情意味,但正是这种渺小而执着的夙愿,让他们在面对麻木冷漠的捐献与死亡时,依然心存美好。这些如同浮士德无限探索后的填海救赎,虽然是茫茫宇宙中的小小星辰,却让人叹息之余又感动着。
所以两则故事的结尾冷静而又充盈着些许温度:
“冬去春来,年复一年。机器人还是坐在原来的地方,发出哭泣的声音。渐渐地,机器人身上长出了锈,发声的部位也开始生锈了。有一天,哭声终于停止了。现在,机器人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坐在小屋边。”
——矢野彻《密友》
“我只等了一会儿,然后钻进车里,驶向我应该待的地方。”
——石黑一雄《别让我走》
注释:
参考文献:
[1]黄莹.迫害还是保护:论石黑一雄作品《别让我走》中的叙事判断[D].江西师范大学,2013
[2]刘国艳.分裂的风景[D].华东师范大学,2016
[3]周颖.创伤视角下的石黑一雄小说研究[D].上海外国语大学,2014
[4]杜明业.《别让我走》的文学伦理学解读[J].外国文学研究,2014
[5]徐睿.新科技时代下的伦理困境[D].南昌大学,2015
[6]矢野彻.《密友》(没找到纸质读本,来源于电子版本)
[7]石黑一雄.《别让我走》朱去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8]蒋风.中日儿童文学交流的回顾及前瞻[J].文科教学,1995
[9]吴占军 尹锦花.日本科幻动画的摇篮期[J].吉林艺术学院学报,2002
[10]袁琳艳.建国以来日译中文儿童文学类图书的译介及出版[J].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学报,2015
完稿于2018.08.30 上海交通大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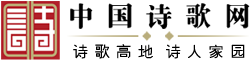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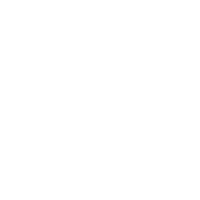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34246号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34246号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