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声咳嗽后,父亲起了床。
窗外的天有些灰蒙蒙的,星子敛去,独独剩下一轮镰刀似的孤月于云层之间若隐若现。耳畔传来几声高昂的鸡鸣,随后是几声低沉的狗叫声。
这之后不久,我再次听见父亲在院坝里的咳嗽声。
我总是能听见父亲那轻微又显得谨慎的起床前的咳嗽声。父亲的肺不大好,长久以来,起床咳嗽的习惯已然被他日渐衰竭的身体所接受。在一片蒙蒙的暗中,我把目光再次投向天边。侧听着,父亲的咳嗽声愈来愈远;眼见着,天边的月亮也似乎愈来愈小、愈来愈暗。
父亲又要去站岗了,戴着蓝色的口罩和红色的袖章,拿着他曾经细细研究过又向我“讨教”如何使用的体温枪,几个星期如一日地站在年前刚刚铺上柏油的村口大马路上。
父亲是一名共产党员,同时,他也是一个普普通通在田地里劳作的普通农民。现在,父亲又成了一名守护乡村的站岗“志愿者”。
印象中,父亲性子执拗又不喜言谈,为此,母亲常骂他是块闷在茅厕里的臭石头。每当母亲诘问他时,父亲便把嘴唇紧紧地抿上,拧成疙瘩的眉间像是积郁了一股化不开的黑墨。父亲从不反驳,等到母亲骂累了,他便把紧紧抿着的嘴巴拉出一个好看的弧度,眉间积郁的那团浓郁的墨便在顷刻间化为潺潺的清泉。
前几天,我去看过父亲站岗的样子。身材矮小的父亲裹着浅绿色的军大衣站在马路边,他那因常年劳作而格外健硕的身体在厚厚的大衣包裹下显得臃肿又笨重。柏油马路是一片深沉的黑,父亲被蓝色口罩遮住的脸也是一片深沉的又红又暗的黑。他的旁边是村委会立的公示牌,黑色楷体,写着“疫情防控,外乡莫入”的字样。父亲手臂上戴着红袖章,疲态的面孔上那双浑浊的眼睛盯着大路的两头。每当有车辆经过,父亲便招手示意他们停下,测量体温,询问路程,登记。父亲对此已非常熟稔了。
我闭上眼,在意识模糊间暗暗猜想,那些过往的车辆看见父亲的同时,是否也瞥见了一块如母亲所说的又黑又丑又硬的大石头呢?
我睡了一会儿,醒来时天已放亮,起床看了看不久前天上那轮镰刀似的弯月,蓝天映衬下已有些看不清了。
母亲在院坝里梳头发,我有意凑近看了看,并不炽热的阳光照在她的头发上,偶尔闪烁几下略微刺眼的银白光亮。
母亲看见我,便咕噜一声,你老子一大早又跑出去了嘞?
我点点头。
母亲把双眼一瞪,眉毛倒竖,你老子一天到晚搞那些,愣是傻,咋个别个不去就他去?别个喊一下,他就去了?站那几天,又莫得懒样钱!
好了好了,也是为国家做贡献的嘛。我安慰母亲。
母亲梳好头发,嘴巴又咕噜几句便不再言语。
过了一会儿,母亲招呼我吃饭。待我吃好,母亲把一个热腾腾的饭盒放我手上。
给你老子拿去,愣是傻,站一天也没得个钱。
母亲把饭盒放我手上,一边咒骂着父亲一边出门。我有些愣,妈你到哪地去?
母亲头也不回,外头去玩哈。
爸不是说了吗?这几天不能出门,村里大喇叭也说了……
咋个不准出去?打个牌还不行了?
那你戴个口罩嘛!
我有些着急,可还是劝不住母亲。
过了会儿,我拿着饭盒朝村口站岗的父亲走去。我家离村口有些远,路走到一半,有个认识我的叔叔叫住了我,左娃,你爸爸遭别个打了嘞——
我便用力握着饭盒使劲地跑了起来。
跑到路口时,远远地看见一堆人围在一辆黑色小车边上,人堆里一点红色在我眼中盘旋,那是父亲手臂上的红袖章。
我跑近了,大口喘着粗气,有些无力地喊了一声,爸——
父亲的耳朵动了动,他侧过头,隔着口罩我能感受到那张黑红的脸对我笑了笑。
我心中的慌张便消了大半。
事后,我才知道,与父亲起争执的司机是个发烧的外乡人,父亲照例进行登记,谁知司机却含糊其词不肯配合他。我的父亲是块茅厕里的臭石头,面对司机好说歹说递烟喊哥的行为无动于衷。父亲冷冷地瞪着司机,黑红的脸隐在口罩下让人看不出喜怒。我暗想司机也许在交流中看出父亲软硬不吃的态度,这让他下定决心要溜之大吉。就在司机想乘父亲不备钻进车内时,我的父亲不亏是种了几十年庄稼的人,他眼疾手快扯住司机的胳膊往外一拽,这一拽让司机勃然大怒,他挥起拳向父亲的胳膊和身体打了几下。父亲面对司机发狂的行为并未惊慌,他两只粗壮的大手有力地嵌住司机的身体。事后我曾追问父亲“擒拿”的秘诀,他那似万年丑石般毫无表情的黑红大脸露出一丝我认为颇为羞涩的笑意来。我的父亲挠了挠头,对着我发出低沉的笑声,像对付倔得不行的牛一样,我的父亲说道,不能急,不然会出大麻烦,得和那畜生周旋——可不能大意。
我家早已不养牛,可父亲仍然把“擒拿”秘诀化为他几十年农民生涯积累的知识向我说教。
在那时——经过闻讯而来的村长和村支书地劝说,这场干戈终究化为玉帛。我走到父亲面前,对司机压抑着愤怒。父亲好似看出我的想法,他伸手在我肩膀上拍了拍,示意没事。
我这才略微放心,随后把还散发着热量的饭盒递给父亲。还未等他打开,村支书在旁边递上一支烟,老金啊,这事挺辛苦,多多包涵啊。
我的父亲只是点了点头,并没有说什么。
这时,村支书露出为难的神色,他凑近父亲压低了嗓音,老金啊,你屋里媳妇又拉着人打牌去了——
我站在旁边,想起母亲,有些慌张。
尽管看不见父亲口罩下是何神色,但他的眉头又拧成了一团。
老金,你也晓得嘛,村里要求了不准聚众打牌,你也是个党员分子,你屋里人拉人打牌也不是一次两次了,这事,怎么着也得带个头才行,是不——
父亲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许久,他弹了弹手里的烟,对村支书说道,我去把她拽回来。
我的父亲大踏步地向前走着,他迈步的姿势铿锵有力,原本有些佝偻的身体此刻挺如青松,我的父亲似乎肩挑着某种东西,小如家常蒜皮,大似青山沧海。
我回到家里,心中有些忐忑。
过了大概半小时,我听见巷子里传来熟悉的母亲的声音。母亲带着委屈又气愤的声调咒骂着父亲,她骂父亲吃力不讨好,整天做那些不挣钱的勾当,又骂自己当初怎么就瞎了眼看上了父亲。
我的父亲俨然成为一块沉默的石头,他把口罩摘下,眉头好似拧成一团乱如麻的螺丝,紧紧抿着的嘴唇轻微抖动。父亲和母亲在院坝里站住,母亲看见我,喉咙里发出鬼魅似的冷笑声,你好好读书,以后别学了你爸。
几十年的夫妻生活已让父亲摸清她的底细,为此,父亲照旧不言语。看见父亲有些“孬”的样子,我的母亲无可奈何,只得咕噜几句便进屋了。
待到母亲进屋,父亲的眉头才舒缓下去,他有些无措地站了会,不久后把口罩戴上,对我说了一句,我站岗去了。
我默默地点了点头。
父亲的语气没有什么变化,像一块悬着的石头落地,稳稳当当。
我的父亲是一名共产党员,但他并不身居高位,很多时候,他都是一个在田间劳作在工地上班的普通农民。没有谁来巴结如父亲这般的农民,父亲执拗的性子也不允许他作出会玷污他身份的事。什么是清廉?什么又是刚正?我初中文化的父亲和这些名头相匹配吗?他只是做了自己的事,做了一个在基层生活的党员的事,这些事不过如鸡毛蒜皮一般不足为道,我的父亲,真的配得上这些名头吗?
在那个时候,全民抗疫的关键时刻,如父亲这般站岗的基层党员又有多少呢?他们被记住了吗?谁来为他们谱写一段赞歌呢?
我看着父亲离去的背影,一种无声的肃然而又战栗的感情突然在我胸腔里激荡。我跑到巷子口,盯着父亲有些远的背影,大喊了一声,爸——
父亲转过身,对着我摆了摆手。
我眯了眯眼,眼前涌起一片湿润的绯红之海,而那明晃晃的海底,全是无言着的丑陋又黑红的石头。
窗外的天有些灰蒙蒙的,星子敛去,独独剩下一轮镰刀似的孤月于云层之间若隐若现。耳畔传来几声高昂的鸡鸣,随后是几声低沉的狗叫声。
这之后不久,我再次听见父亲在院坝里的咳嗽声。
我总是能听见父亲那轻微又显得谨慎的起床前的咳嗽声。父亲的肺不大好,长久以来,起床咳嗽的习惯已然被他日渐衰竭的身体所接受。在一片蒙蒙的暗中,我把目光再次投向天边。侧听着,父亲的咳嗽声愈来愈远;眼见着,天边的月亮也似乎愈来愈小、愈来愈暗。
父亲又要去站岗了,戴着蓝色的口罩和红色的袖章,拿着他曾经细细研究过又向我“讨教”如何使用的体温枪,几个星期如一日地站在年前刚刚铺上柏油的村口大马路上。
父亲是一名共产党员,同时,他也是一个普普通通在田地里劳作的普通农民。现在,父亲又成了一名守护乡村的站岗“志愿者”。
印象中,父亲性子执拗又不喜言谈,为此,母亲常骂他是块闷在茅厕里的臭石头。每当母亲诘问他时,父亲便把嘴唇紧紧地抿上,拧成疙瘩的眉间像是积郁了一股化不开的黑墨。父亲从不反驳,等到母亲骂累了,他便把紧紧抿着的嘴巴拉出一个好看的弧度,眉间积郁的那团浓郁的墨便在顷刻间化为潺潺的清泉。
前几天,我去看过父亲站岗的样子。身材矮小的父亲裹着浅绿色的军大衣站在马路边,他那因常年劳作而格外健硕的身体在厚厚的大衣包裹下显得臃肿又笨重。柏油马路是一片深沉的黑,父亲被蓝色口罩遮住的脸也是一片深沉的又红又暗的黑。他的旁边是村委会立的公示牌,黑色楷体,写着“疫情防控,外乡莫入”的字样。父亲手臂上戴着红袖章,疲态的面孔上那双浑浊的眼睛盯着大路的两头。每当有车辆经过,父亲便招手示意他们停下,测量体温,询问路程,登记。父亲对此已非常熟稔了。
我闭上眼,在意识模糊间暗暗猜想,那些过往的车辆看见父亲的同时,是否也瞥见了一块如母亲所说的又黑又丑又硬的大石头呢?
我睡了一会儿,醒来时天已放亮,起床看了看不久前天上那轮镰刀似的弯月,蓝天映衬下已有些看不清了。
母亲在院坝里梳头发,我有意凑近看了看,并不炽热的阳光照在她的头发上,偶尔闪烁几下略微刺眼的银白光亮。
母亲看见我,便咕噜一声,你老子一大早又跑出去了嘞?
我点点头。
母亲把双眼一瞪,眉毛倒竖,你老子一天到晚搞那些,愣是傻,咋个别个不去就他去?别个喊一下,他就去了?站那几天,又莫得懒样钱!
好了好了,也是为国家做贡献的嘛。我安慰母亲。
母亲梳好头发,嘴巴又咕噜几句便不再言语。
过了一会儿,母亲招呼我吃饭。待我吃好,母亲把一个热腾腾的饭盒放我手上。
给你老子拿去,愣是傻,站一天也没得个钱。
母亲把饭盒放我手上,一边咒骂着父亲一边出门。我有些愣,妈你到哪地去?
母亲头也不回,外头去玩哈。
爸不是说了吗?这几天不能出门,村里大喇叭也说了……
咋个不准出去?打个牌还不行了?
那你戴个口罩嘛!
我有些着急,可还是劝不住母亲。
过了会儿,我拿着饭盒朝村口站岗的父亲走去。我家离村口有些远,路走到一半,有个认识我的叔叔叫住了我,左娃,你爸爸遭别个打了嘞——
我便用力握着饭盒使劲地跑了起来。
跑到路口时,远远地看见一堆人围在一辆黑色小车边上,人堆里一点红色在我眼中盘旋,那是父亲手臂上的红袖章。
我跑近了,大口喘着粗气,有些无力地喊了一声,爸——
父亲的耳朵动了动,他侧过头,隔着口罩我能感受到那张黑红的脸对我笑了笑。
我心中的慌张便消了大半。
事后,我才知道,与父亲起争执的司机是个发烧的外乡人,父亲照例进行登记,谁知司机却含糊其词不肯配合他。我的父亲是块茅厕里的臭石头,面对司机好说歹说递烟喊哥的行为无动于衷。父亲冷冷地瞪着司机,黑红的脸隐在口罩下让人看不出喜怒。我暗想司机也许在交流中看出父亲软硬不吃的态度,这让他下定决心要溜之大吉。就在司机想乘父亲不备钻进车内时,我的父亲不亏是种了几十年庄稼的人,他眼疾手快扯住司机的胳膊往外一拽,这一拽让司机勃然大怒,他挥起拳向父亲的胳膊和身体打了几下。父亲面对司机发狂的行为并未惊慌,他两只粗壮的大手有力地嵌住司机的身体。事后我曾追问父亲“擒拿”的秘诀,他那似万年丑石般毫无表情的黑红大脸露出一丝我认为颇为羞涩的笑意来。我的父亲挠了挠头,对着我发出低沉的笑声,像对付倔得不行的牛一样,我的父亲说道,不能急,不然会出大麻烦,得和那畜生周旋——可不能大意。
我家早已不养牛,可父亲仍然把“擒拿”秘诀化为他几十年农民生涯积累的知识向我说教。
在那时——经过闻讯而来的村长和村支书地劝说,这场干戈终究化为玉帛。我走到父亲面前,对司机压抑着愤怒。父亲好似看出我的想法,他伸手在我肩膀上拍了拍,示意没事。
我这才略微放心,随后把还散发着热量的饭盒递给父亲。还未等他打开,村支书在旁边递上一支烟,老金啊,这事挺辛苦,多多包涵啊。
我的父亲只是点了点头,并没有说什么。
这时,村支书露出为难的神色,他凑近父亲压低了嗓音,老金啊,你屋里媳妇又拉着人打牌去了——
我站在旁边,想起母亲,有些慌张。
尽管看不见父亲口罩下是何神色,但他的眉头又拧成了一团。
老金,你也晓得嘛,村里要求了不准聚众打牌,你也是个党员分子,你屋里人拉人打牌也不是一次两次了,这事,怎么着也得带个头才行,是不——
父亲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许久,他弹了弹手里的烟,对村支书说道,我去把她拽回来。
我的父亲大踏步地向前走着,他迈步的姿势铿锵有力,原本有些佝偻的身体此刻挺如青松,我的父亲似乎肩挑着某种东西,小如家常蒜皮,大似青山沧海。
我回到家里,心中有些忐忑。
过了大概半小时,我听见巷子里传来熟悉的母亲的声音。母亲带着委屈又气愤的声调咒骂着父亲,她骂父亲吃力不讨好,整天做那些不挣钱的勾当,又骂自己当初怎么就瞎了眼看上了父亲。
我的父亲俨然成为一块沉默的石头,他把口罩摘下,眉头好似拧成一团乱如麻的螺丝,紧紧抿着的嘴唇轻微抖动。父亲和母亲在院坝里站住,母亲看见我,喉咙里发出鬼魅似的冷笑声,你好好读书,以后别学了你爸。
几十年的夫妻生活已让父亲摸清她的底细,为此,父亲照旧不言语。看见父亲有些“孬”的样子,我的母亲无可奈何,只得咕噜几句便进屋了。
待到母亲进屋,父亲的眉头才舒缓下去,他有些无措地站了会,不久后把口罩戴上,对我说了一句,我站岗去了。
我默默地点了点头。
父亲的语气没有什么变化,像一块悬着的石头落地,稳稳当当。
我的父亲是一名共产党员,但他并不身居高位,很多时候,他都是一个在田间劳作在工地上班的普通农民。没有谁来巴结如父亲这般的农民,父亲执拗的性子也不允许他作出会玷污他身份的事。什么是清廉?什么又是刚正?我初中文化的父亲和这些名头相匹配吗?他只是做了自己的事,做了一个在基层生活的党员的事,这些事不过如鸡毛蒜皮一般不足为道,我的父亲,真的配得上这些名头吗?
在那个时候,全民抗疫的关键时刻,如父亲这般站岗的基层党员又有多少呢?他们被记住了吗?谁来为他们谱写一段赞歌呢?
我看着父亲离去的背影,一种无声的肃然而又战栗的感情突然在我胸腔里激荡。我跑到巷子口,盯着父亲有些远的背影,大喊了一声,爸——
父亲转过身,对着我摆了摆手。
我眯了眯眼,眼前涌起一片湿润的绯红之海,而那明晃晃的海底,全是无言着的丑陋又黑红的石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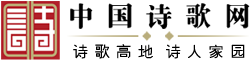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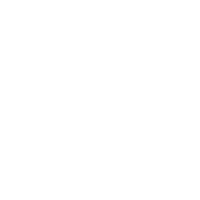

 (5次)
(5次)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34246号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34246号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