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歌从《诗经》、楚辞、汉乐府,到唐诗、宋词、元曲,到新诗百年,继承和创新,因袭与嬗变,源远流长三千多年。远的不说,单就新诗而言,百年来中华民族每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都有诗人在呐喊,在呼号,在歌唱。然而百年来新诗又常常遭遇质疑和诘难,至今仍在不断的争议声中步履蹒跚。
回首新诗百年,诗坛百感交集。第一,回首百年,新诗高峰叠翠,其中不乏众多经典之作。第二,中国新诗百年发展史,其实就是一代又一代诗人从草根走向主流的蝶变成长史。第三,随着网络化,新诗民主化时代正在或者已经到来,人人心中都有一首诗,伟大的作品、伟大的诗人化茧成蝶,呼之欲出。
一、致敬中国新诗百年 百年新诗发轫于五四新文化运动
百年新诗发轫于五四新文化运动。1917年2月《新青年》刊出胡适的《白话诗八首》,被公认为中国新诗的起点。“两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从遥远的古体诗时代一下子飞到了白话诗的新时代。1920年胡适出版《尝试集》,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诗集诞生。不过真正让后人记住的不是这首《蝴蝶》,而是另外一首《希望》,后来由诗而歌改名为《兰花草》,经由台湾青春小歌后卓依婷深情演绎,流传甚广。普罗大众这才知晓原来胡适为中国新诗的开端。
后来又有人提出不同意见,说中国新诗的开端和起点不是胡适而是鲁迅。并举鲁迅的《野草》开篇《秋夜》的第一句:“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二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以为佐证。说如此分裂与重复的句法才更像一首新诗。这纯属个人之见。其中大约隐含着对胡适新诗的失望。
至此,百年新诗大体可分为五个时间段:新文化运动启蒙期、建国前后的革命英雄主义浪漫期、文革后的朦胧苏醒期、80-90年代的诗歌狂热期、及至新世纪前后绵延至今的草根网络期。无论是文化启蒙,讴歌革命,关注时代主题还是注重个人感受,新诗高峰迭起,一波又一波,优秀诗人和优秀作品不断涌现,汇成浩瀚壮观而又不免泥沙俱下的新诗海洋,引起文学界一阵阵感叹。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欧洲文艺复兴何其相似,或者说原本就有西学东渐的基因,批判社会的种种腐朽,呼唤人性的自由解放,鼓动民众顺应时代变革,用光明驱除一切黑暗。这一时期以胡适为开端,以郭沫若为代表,还有追捧徐志摩爱情诗的另一部分人,以及丁玲的小思绪,充当了新诗启蒙的先行者。
郭沫若的《凤凰涅槃》,激情澎湃,斗志昂扬,极富批判思想和启蒙意识,彰显强烈的革新精神,“凤和凰的死期将近了”,可是他们宁愿死去,也要选择涅槃重生,可以说为旧时代敲响了丧钟,为新时代吹起了号角。
民主战士闻一多,倡导新诗格律化,主张“戴着镣铐跳舞”,让新诗不失音乐之美。其代表作《七子之歌》,忧患重重;另一首《死水》,皆因“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诗人拍案而起,为民主殉难。
新月派徐志摩,一生为爱痴狂。《沙扬娜拉》,“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再别康桥》,“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掀起波光潋滟,激起心绪涟漪,甚或波澜,仿佛恋爱中的徐志摩喃喃私语,关于陆小曼,关于林徽因,关于其诗背后的爱情故事,成为后人津津乐道的话题。可惜诗人因飞机失事而英年早逝,人间最美四月天,转眼花落流水去,让人扼腕叹息,期待不了一个圆满的结局。
正如寂寞又彷徨的戴望舒,迷茫苦闷找不到出路的知识分子,《雨巷》,《我的记忆》,开启了现代诗派,诗人却沦落为寂寞暗夜的太息者和哀怨人。
丁玲的《繁星》、《春水》,一扫阴郁之气,句式短小,灵光乍现,粗看不成体制,细读充满火花,还真如天上的繁星,一闪一闪亮晶晶,又像解冻的春水,叮叮咚咚,让人情思环绕,怦然心动,自成一片天地。这种泰戈尔似的奇妙短章,也告诉着后人作诗其实也并非什么难事,绝非难上加难,只须敢于提笔,捕捉一个个灵感而已。就像小时候在夏夜里追逐萤火虫,只要敢于动手去抓总会有一番收获的。我们称之为丁玲的小思绪,正是形象得恰如其分。
国共内战及延安抗战时期,光未然的《黄河大合唱》、田汉的《义勇军进行曲》,尤其是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我深爱这土地》,语调铿锵,笔力雄浑,讴歌时代,汪洋恣肆,有一种独特的散文之美。臧克家,号称泥土诗人,善于抒写农村题材,笃定生活是诗的土壤。贺敬之《回延安》,融合了陕北民歌信天游的形式,语言质朴,生活气息浓厚,感情炽热,极富音乐之美。这一时期的革命浪漫主义诗歌,工农兵题材,抗战主题,英雄精神,代表着最广泛的四万万同胞的呼声和共同命运,是那个时代轰轰烈烈的大音希声。
总体来看,从白话诗诞生,至新中国成立,若论新诗之最高成就者,还属毛泽东无疑。不论从其领导地位,文艺思想,诗歌成就,时代影响来说,都是当之无愧的。唯其一点,毛诗皆为古体,似乎称不上“新诗”。然而“新诗”之所以为新诗者,并不完全拘泥于古体或自由体,文言或白话。应该说新时代的人所作的新时代的诗,今天的人所写的今天的诗,皆可归位于“新诗”。
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不但开创革命诗派(应该说对革命诗歌有重大影响,点燃了一把大火,其诗言志,抒情,写景,状物,催人奋进,令人向往),更有领袖群伦、舍我其谁之气概,之气魄,之气势,之气度。也难怪蒋介石发动全党全国之力,欲与天公试比高,然无人有此雄壮之心,无人有此博大之心胸和襟怀,纵是想破了脑袋也枉然。
其后改革开放,80年代诗歌狂潮,朦胧诗异军突起。然而斯时的朦胧诗终归是有些“朦胧”,大多晦涩,不顺畅,情绪灰色,让人直呼看不懂。大约都是中了西方诗的流毒。穆旦等人的翻译诗就有这种毛病。象征寓意驳杂,极不适合国人口味。卞之琳是个意外,他一心追求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一生作诗不过五千余言,算得上一个字斟句酌、惜墨如金的苦吟诗人。其《断章》:“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堪称新诗锤炼字句的绝佳典范。
大约同一时代的台湾新诗,余光中、郑愁予、洛夫等人,强调“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然而他们最后都回归了传统。余光中后来更是宣称“我的血脉中有一条黄河的支流”,此生“要做屈原和李白的传人”,其代表作《乡愁》哪里还看得见西方诗的影子?完全是古典的音乐诗,情深意长,音韵动人。
这一时期的代表性诗人,北岛,顾城,以斗士姿态走上诗坛,又随之淹没于汪洋大海。原本艰难曲折的生动故事,却酿成难以谅解的人生事故。北岛的那首《回答》:“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道出了一个有着极重自卑感的斗士内心踯躅的英雄情结,可是漂泊流浪的心却再也回不去。顾城的那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因其不健全的人格而诗格自然被遗忘殆尽。偶有论者为其发声,真不知其意何谓。
朦胧诗的真正代表,当属席慕容和舒婷。细看舒婷之诗,说朦胧其实并不朦胧,同时代的年轻人大多还是能会其意的。虽有多种解读,大意应该不会错也不太差的。《双桅船》,《致橡树》,风靡一时,并非晦涩到让人读不懂,乃至产生误解或曲解。倒是同时代其他更多的诗人,走入了朦胧诗晦涩的死胡同。
某些朦胧诗晦涩到让人看不懂,约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有意为之,所谓曲意难解,说白了就是不愿与你凡夫俗子为伍。另一种是无意为之,说白了就是思想还不够捋顺,意象还不够鲜明,表达还不够到位,心里也想说的明白点,可是诗做出来不是想象中的样子。自己一本糊涂账,大众自然不买账。
接下来有一位诗人,号称“北大三杰”的海子,在此须要提一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多么美好的理想,多么美好的憧憬,多么美好的咏叹!可惜诗人总是缺什么写什么,心中怎么渴望嘴里怎么呼喊。海子终其一生并未遇见春暖花开,临终也不是面朝大海,而是选择了一处关隘。山海关,天下第一关,真是颇具新诗的意境和象征。面对关隘,相信海子内心也彷徨过,犹豫过,忐忑过,可他向往不了戴望舒的雨巷,尚有油纸伞,尚有丁香花,尚有撑着油纸伞像丁香花一样的姑娘。海子面对的是关,这个关生死重重,到底该过该留,该进该退,该生该死,挣扎,纠结,绝望!最后海子以死成就了一首悲怆的诗!
学院派诗人王家新,西川,欧阳江河,臧棣等,因崇尚西方现代主义而走向先锋探索,其诗颇多意象和象征,后来也有适度口语化。大约是学养太深,他们的诗如佛,如道,如理,凡人一般参不透,因此也就少有人去参、去悟、去透。大约他们写诗的时候也没想着让太多人看明白,惟愿在小圈子里流传。正因为看不懂,普罗大众也就不想看,不去看,不看白不看,看了也白看。譬如西川,复杂的思想,含混的意识,驳杂的散文化倾向,各种不确定性包罗万象,什么意思都有,具体什么意思一般无人知晓也无从知晓,只有去猜。把诗写到这种技术层面着实令后人仰视。王家新的诗更纯净一些,也更纯粹一些。
然而诗不就是给人看的么?难道只给心仪的师友们看?诗还须反映普通人的情感,普通人的遭遇,普通人的梦想。通俗易懂的,大众喜爱的,脍炙人口的,才能流传下来,流传开来。诗歌界曾有一段公案,证明笔者所言非虚。
有很多人非常看不起那个掀起过诗歌风暴的汪国真。欧阳江河曾说:汪国真的诗全都是“假诗”,汪诗对中国当代诗歌唯一的作用就是阻碍,对学生是一种毒害,是一种“恶趣味”,羞于被称为汪国真同一时代、使用同一语言的诗人。更有甚者,说汪诗是“生命能够承重之轻”,是文化贫瘠的反映,直斥汪诗为垃圾,为手纸,为小儿科,为不入流。这些话恶劣到极致。不过有一点歪打正着说对了:今后写诗还真就像吃喝拉撒睡,绝不是什么神秘莫测的事。
毋庸讳言,欧阳老师他们的学术精神无疑是值得尊敬的,可是他们评论汪诗的这些话却显得极为可疑。就像中国房市的专家,股市的大咖,总也号不准房市或股市的脉。我们的意思是说,他自己却并没有哪怕一首可称之为经典的诗让人记住他。亦无特别出色的作品引领风尚。就像汪诗《年轻的潮》一样。
汪国真的诗歌简短而寓意明晰, 昂扬而又超脱,清新的笔法和细腻的感情比之前的“朦胧诗”更浅吟低唱,更通俗易懂,20多年来一直倍受青年人喜爱,就是对中年人也有很大激励作用。笔者身边至今还有不少人以汪诗的名言警句为座右铭。其诗集销量总版印数超过600万册。说他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似乎一点也不为过。“汪国真现象”为时代创造了大量的读者、作者和诗歌爱好者。“汪国真热”称得上那个时代经典的文化符号之一。此后的余秋雨,于丹,易中天,直到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也许还有韩寒,郭敬明,余秀华,网络文学IP热,都要稍逊一筹,没人达到汪国真的热度。或许唯有“超女”可比。
然而却有太多的“他们”看不起他。当今诗歌某种程度上被边缘化了,用汪国真的话说,“观众已经走光了,演员还在台上装腔作势”。“他们”这些人对新诗一定程度上的边缘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第一,你没有比别人更高明,写出一批质量口碑俱佳的作品来;第二,你走入了小圈子,也根本没有口传心授,用过硬的作品教育读者怎样去读诗,怎样去作诗;第三,你看不起汪国真不就是看不起广大的年轻读者么?现在追看“中国诗词大会”的,有几个不是当年汪诗的粉丝或者汪诗的粉丝的下一代?毛主席曾说熊向晖一个人能抵三个师。依笔者所见,汪国真对新诗的普及贡献,抵得上“他们”所有的一大群人。
很遗憾没人接下汪国真的棒。“现在的读者不是不喜欢诗,而是不喜欢那些装腔作势的诗”。“深刻的、崇高的、有水准的 ”诗歌,看来还是用浅显易懂的汉语表述出来为最好。都说青年是祖国的未来,可是对青年的喜爱你却不赞同,甚至批评抨击,岂非自相矛盾,一味站在个人的立场说话?俞伯牙和钟子期,高山流水遇知音,子期病逝,伯牙摔琴,知音不再,弦断有谁听?其实俞伯牙那首曲子,凡人也是能够听懂的,钟子期不就是一个樵夫嘛!《高山流水》至今满大街流传,几乎人人耳熟能详。当年伯牙毁琴烧谱,成就一段曲终人散的佳话,盖因慕名清高不肯“同流合污”者也。今人还有谁欲东施效颦耶!
接下来可谓新诗的群星闪耀时刻。一大批卓有成效的诗人,写出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口语化新诗。他们各有所长,各有风格,各有代表性群体,各有自己赖以成名的代表作,目前都已走上诗坛主流地位,领导或主导着一席之地。他们经过艰难摸索,经历过崇拜洋诗的先锋时代,又逐渐回归到中国古典诗词文化里去寻找和汲取营养。以笔者有限的视野和观察,特选取几个尚在主流圈层的大门内外徘徊的草根诗人,我们姑且称之为后起之秀,做一简单探讨。
譬如扎根于彩云之南的雷平阳,珠三角的打工诗人郑小琼,长三角台州湾的柯健君,山西太行山的勘探诗人张二棍,中部已然崛起然而始终摇摇晃晃的余秀华。也不妨提一提刚刚开始步入诗坛的创业诗人高盛。
雷平阳出名早,评论其诗者大有人在,读者皆为其云南特色着迷。柯健君位于浙江台州,笔者与其并无深交,因为一次全国性的诗文笔会结识于天台山,然其所赠之诗集逐一浏览拜读过,尤喜他《在海边》的一系列吟唱。
在此想着重说说郑小琼。郑小琼的打工诗,像“五金厂的铁一样冰冷”,然而却自有温度。数千万打工仔打工妹,比之全国的中学生大学生,群体也不算为小。打工者的经历,经验,故事,心事,情绪,表情,理想,梦想,喜怒哀乐,嬉笑怒骂,有太多的角度可以入诗,多少个黄麻岭也载不动,装不下。然而郑小琼步入诗坛红起来也有好多个年头了,诗集也出了十多本了,却一直没能大红大紫,虽有一方话语权,终因学历、见识、思考之短板,并未迈入真正的主流(或者郑小琼是主流的,笔者这样说并无任何恶意,更多的是抱憾和反思)。
写诗最关键看发轫期和成熟期。郑小琼在发轫期获得追捧,在成熟期相对来说受到主流诗坛的关注度不够。囿于一隅摸着石头过河。郑小琼的诗歌,缺失进一步深挖的自觉,缺失为打工群体代言的担当胸怀,缺失主流诗坛的专家会诊,而这些主流专家特别是作协的专家们是有这个义务的。主流诗坛的关注和帮扶不够,而且总是滞后,一首歌已唱完了,捧哏还没登场。留作盖棺定论耶?正确的做法是研讨之,剖析之,助推之,方可经典化,竖起新诗的丰碑。
郑小琼的诗歌若能站在打工者角度,描摹抒写之外,更多社会学思考,成为打工一族真正的代言人,流传必定更广,社会影响必定更大,也必定更能接近新诗皇冠上的明珠。推而广之,在我们这个时代,伟大的诗人,伟大的作品,常常就是这样擦肩而过或者偃旗息鼓的。如果主流诗坛不能提前发现基层的苗头与动态,并辅之以无微不至的培育和关怀,我们终将剩下空空的叹息。
余秀华的诗歌赤裸,坦率,突破框框,毫无顾忌,颇多出格之语,借此走红诗坛。有人谩骂她的诗大部分都是艳诗,甚至是“荡妇体”。余秀华毫不在乎,“荡妇就荡妇”,更显出诗人的可贵与坚守。愚以为余秀华出名,草根的同情多于主流的赞赏。然此非主因,顶多算一偏门,但绝不是意外。余秀华诗歌提振人心的精神,在于她拖着一身病躯坚持发出自己的声音!那首最引人注目也最让人诟病的《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其实写的很好。那个“睡”字如果换成一个“爱”字,有何不可?一个“爱”见怪不怪,一个“睡”惊世骇俗,石破天惊!诗人宁愿出此下策,冒着毁灭自己的风险,也要博取主流诗坛“赞赏少于同情”的关注。如此艰辛的成名之路,想当年贾平凹,陈忠实都碰到过,命运何其相似乃尔!这种故事将来还会不断上演。福兮祸兮?幸与不幸耶?
自诩“看破中国式创业,领教中国式商道”的创业诗人高盛,前半生执着于创业,人到中年心血来潮步入诗坛,原本虾兵蟹将一个,欲在前人不曾跋涉的创业领域开辟一隅,以期写出言之有物、有血有肉的新诗来。“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梦叫中国梦,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诗叫创业诗。给创业一点诗意,无论得意还是失意”。然其功力尚浅,浅尝辄止,自知诗才有限,不如专攻小说一途,探索做创业文学,美其名曰创业小说,志不在小。此路能否走通尚有九九八十一难,十万八千里行程,就看能否习得孙猴子的筋斗云,暂且不提也罢。
二、何为主流?何为草根?不管从作者、读者、评者哪个角度看,百年新诗都是蔚为壮观的
不管从作者、读者、评者哪个角度看,百年新诗都是蔚为壮观的。中国新诗百年发展史,其实就是一部草根诗人走向主流的蝶变成长史。
何为主流?何为草根?所谓主流与草根之称谓,实属强加于人的一种勉强。正如太极之阴阳,手掌之两面,彼此彼此,互为依存,而绝难割裂开来。主流都是从草根一步一步崛起的,崛起之前的主流谁没做过草根?现在的问题是,随着网络诗歌的快速崛起,主流压不住草根,草根却很有颠覆主流之势。
所谓主流,第一身处主流,居于主要城市,身为主流人群(作协派,学院派,媒体派),处于庙堂之高,而非江湖之远;第二拥有一方主流阵地(报刊,出版,评论,网络),主流渠道(纸媒,电媒,网媒,教科书),哪怕一个小小的区域,小小的平台,小小的阵地,最关键的手中有笔,可判生死,府中有粮,饿不着冻不着;第三开口必为主流话语,以期发出主流声音,凤凰来仪,流播四方,百鸟朝凤,万国朝贡。除此之外,其他的大抵都算作非主流的草根派。
所谓草根者,非主流也。非茎非叶,非花非果,不过草芥之末。荒野田边,河坡沟岸,偏僻蹊径,砖石墙角,野蛮生长,比比皆是。当春破土而出,临冬枯萎入泥。盛时疾风劲吹,败时零落凋蔽。白居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说的是草根。然笔者所言之草根,并非原上之根深叶茂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有草葳蕤而为草原,绝非一般草根。真正的草根,往往是土生土长的,自生自灭的,偶尔开一小花,装饰门面,点缀天涯,并不夺人光辉。
草根乃未名之末者,人微言轻,既非作协名家,亦非学院名师,更非媒体代言人,自诩草根者大多懂得夹起尾巴做人,有时心血来潮大约也作诗。
我们今天所说的草根,更多的是一种譬喻。喻为散落于民间的草根诗人。正常情况下草根诗人躲藏遮掩犹未不及,何敢曝光于众目睽睽之下侃侃而谈?皆因当今网络科技之发达。草根一派不同于主流诗人,整天穿梭于各种会场、酒场脱不开身。草根诗人身为草根,自然而然倾心于为草根写诗,他们一般热衷于网络媒体(论坛,博客,微博,微信,QQ,APP,朋友圈),因为他们实在也没有其他的地方可去。其他地方都是主流诗人的天下。幸得网络气氛也很热烈,整天里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交流切磋,刷存在感,不服就放马过来比试,生动活泼比主流还主流,也因此草根的根须可以绵延不断,不致于倒地萎顿。
现在主流诗坛多忧虑新诗越来越边缘化了,草根诗人们却说新诗早已“赶唐超宋”。君不见网络诗歌有增无减,热度正酣,何来边缘化、小众化、消失论之担忧?中国历史上有哪个朝代让文学特别是诗歌这样繁荣过?曝光过?没有!只有今天!多少学文的,不是学文的,都对诗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写诗,读诗,爱诗,正在成为一种时代风尚。种子已埋下,有苗不愁长。
当然,网络上的草根诗人,无论其人还是其诗,注水的成分也不少。新诗气短,好作品缺失,经典化稀有,诗作虽以海量计,大众公认的好诗却没有几首。广泛传播开来的更是少之又少。诗歌之美,美在遣词造句,美在韵律节奏,美在赏心悦目的外观形式,更美在语言文字背后的诗人的心。经典的,口语的,千锤百炼的,野蛮生长的,有文化担当的,侧重于娱乐的,都可有好诗。
人们对新诗诘难,本质上还是对草根的蔑视,不屑,不尊重。人们总是习惯于站在一种看似“主流”的立场来批判新诗,殊不知新诗从一开始出生就是个草根派,至今也仍然是。虽然诗坛上有大把的所谓“主流诗人”。远的千年前,李白是个放逐者,杜甫是个落魄者,孟浩然是个隐居者,李商隐是个失意者,他们都不曾贵为主流,顶多算个门客,主流之光,昙花一现。近的百年前,胡适、郭沫若,哪个不是不折不扣的草根派?因为那时还是古体诗的天下。
中国新文学史上,鲁迅、巴金、老舍等名家,他们当时都是社会上并非主流的一小撮人,起初的创作道路都走得很艰辛,都是在各种质疑和争议中从草根步入主流的。鲁迅是弃医从文的,巴金是学外文的,老舍是大杂院出来的,后来的莫言,余华,阿来,严格来说皆非科班出生,最多算得上半路出家,他们都是一辈子自己教自己,完全靠自学,然而他们最后都成为“天生的作家”,成为天生为写作而生的人,成为中国文学界的中流砥柱乃至旗帜。
新时代的诗人中汪国真很有代表性。当年《诗刊》的编辑唐晓渡曾回忆说,“汪国真的诗,九个编辑里没一个重视的。”即便在后来“汪国真热”席卷全国之后,“主流”文学刊物仍然拒绝刊发汪国真的诗作,主流文学界对汪诗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冷漠,诗评家们也大都保持沉默。慧眼不识珠,伯乐不相马,扶植新人成为一句令人啼笑皆非的空话。那些孤芳自赏的所谓主流,在“汪国真热”普及新诗的过程中沾尽了风光,从而确立了自己牢固的诗坛主流地位。
汪诗被嘲笑,挖苦,贬低,不予重视,褒少贬多,与读者反馈和市场反应截然相反。“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我微笑着走向生活”,却并没有几个主流诗人吟得出。这正说明汪诗与时代保持着与时俱进,而主流们却日渐疏远了自己的核心客户群。汪诗的社会影响力被严重低估了。其所起的作用或许是莫言都无法替代的。汪国真进入主流诗歌史天经地义,这个里程碑式的记忆,任谁想抹杀也抹杀不了。
那些看不起汪诗的同行,我们不妨称之为文化诗人。他们大都把诗当作文化的载体,一生坚持与诗对话,他们的智商是超级的,知识是渊博的,学养是深厚的,然而他们并不是活蹦乱跳的、烟熏火燎的、知冷知热的诗人。他们大约从小考、中考、高考一路过关斩将,学士、硕士、博士一路领先同侪,讲师、教授、博导一生顺遂无虞,没有名落孙山的揪心,没有饥寒交迫的窘境,没有弹尽粮绝的考验,书香茂盛而生活贫瘠,他们的生活就是书,书就是生活,没有基层打拼的生死体验,当然也就写不出大众喜爱的诗来。他们虽然能感受和预知,然而却难以体验某种刻骨铭心的热爱或者痛苦。当然这不是他们的错。
因此,他们写诗其实就是论诗,多理性,多思辨,继承了朱熹的衣钵,擅长于教诲、品评和堆砌,唯独少了草根的生态和草香的味道。他们的诗肯定侧重于诗艺,说白了就是炫技。晦涩的太晦涩,浅白的不屑为。然而,赋比兴比不过诗经,意识流比不过楚辞,善用典比不过杜甫,格律精准比不过唐诗,音乐传唱比不过宋词,轻松活泼比不过元曲,正如李太白登黄鹤楼时所感叹: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李太白的诗天然去雕饰,他们更是学不来的。
主流们正确的做法是融入草根,老老实实承认自己从前也是个草根,谁并不比谁高明多少,关注他,接纳他,包容他,直至融入其中,同呼吸共命运,身先士卒,做出表率,写出一批有号召力、有影响力的作品来,扶持基层草根创作,践行传帮带三部曲,提前发现,深入挖掘,引导之,成熟之,共同推动新诗向下一个百年发展。张艺谋,莫言,余华,当年也是没人愿意荐之,无奈只得出口转内销,落得一个专门揭露国人阴暗面的礼帽。作品还是那个作品,有人开始言必称之,鞍前马后扶之坐庄。批判的是那批人,追捧的还是那批人。这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墙内开花墙外香的事,真不希望看到在家门口轮番上演。
主流们内部也常常有不同的声音。有褒奖的,有质疑的,有拥护的,有反对的,有时会吵得很激烈,针锋相对,相互掐架。譬如对新诗的开创者胡适,有些人奉若神明,有些人不以为然,有些人就很看不起。不过这些人品评新诗臧否人物,面子上惊涛骇浪,里子上轻描淡写,激不起什么醒目的水花。
纷纷扰扰的新诗纷争,归根结底是话语权之争。格律体自由体之争,中国诗外国诗之争,主流派草根派之争,谁主谁次,孰优孰劣,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诗人说诗人有理,读者说读者有理,纷纷攘攘,莫衷一是,千姿百态,不足为怪。说白了都是话语权之争。作者,读者,编者,评者,各有各自的立场,各有各自的圈子,各有各自的利益,人人都想当老大,让别人服从自己的意志,但总缺少当老大的风范。老大要么扶持人,要么发现人,要么领导人,要么服务人,可是这种瞻前顾后乐相马、俯首甘当孺子牛的老大到现在还没出现。
其实,遵从格律是好诗,自由洒脱也是好诗;西洋诗意象优美,中国诗意境更美;主流诗人写得一首好诗,草根诗人偶尔也有上佳的发挥。格律并非好诗的唯一标准,语言也并非好诗的唯一标准,好诗的唯一标准是诗意,诗人心底的诗意,读者读到的诗意,二者缺一不可,缺一不成其为诗意。新诗诗意之美,可大可小,可远可近,可内可外,可虚可实,亦明亦暗,亦正亦邪,天地环宇,包罗万象,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诗意之美,正如百舸争流,百花争艳,百鸟争鸣,可以极大地满足诗者、读者、编者、评者的各自审美。
然而诗意并非诗艺。新诗要表达大众理想还是个人理想?新诗要走入大众化还是小圈子?新诗要走入更加广阔的空间还是死胡同?这不是一个选择题,也不是一个填空题,而是一个权衡兼顾的论述题。无论现实主义还是浪漫主义,无论主流诗人还是草根诗人,一首新诗问世,其诗意或诗艺的强弱好坏,唯一的裁判是读者,而不是诗人自己。一个诗人无权评判自己的作品,正如一个人不能左右自己的命运。你的诗意好,读者有感觉;你的诗艺好,读者有感受,二者必居其一。如果诗意或诗艺并未捂热,读者毫无体验,任你孤芳自赏,敝帚自珍,读者现在看不懂,将来也不会看。你的付出只能默默压在箱子底。
虽然诗意并非诗艺,但是诗人的诗意却要借重于诗人的诗艺得到自由任性的发挥。李白的诗意好,“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一读就能感觉到。贾岛的诗艺好,埋头琢磨“僧敲月下门”还是“僧推月下门”,结果冲撞了韩愈的仪仗,也因而有了“推敲”之佳话。杜甫诗意与诗艺俱佳,“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让人叹为观止。
诗意可捕捉,诗艺可修炼,当今看不明白的诗歌生态更让人担忧。新诗已被逼上全面深化改革的风口浪尖。若不伤筋动骨,肯定收效甚微。绝非巡视整改就可轻易收兵。第一,新诗的产出模式不妨借鉴供给侧改革。主流诗人既有阵地,草根诗人网络平台,顺其自然还是弥合边界?鼓励发展还是横加阻拦?质疑诘难还是容错纠偏?放开数量还是锤炼质量?看起来涉及主流非主流话语权之争,其实显现了体制机制之利弊。新诗盘子已经很大了,体制机制几十年不变,主流诗人有垄断之弊(最为诟病的是小圈子生态,新诗发表和出版主要看谁的脸熟),草根诗人有拼凑之嫌(主要存在粗制滥造、急功近利等毛病),根深蒂固,难以撼动。供给侧改革的妙处,在于淘汰落后产能,扶持有创新活力的经典品牌。作为新诗最大产出量的主流派和草根派,按图索骥不难药到病除。
四川省作协主席阿来的一段话或许很有代表性:“四川人口多,写作资源很丰富,四川的文学不应该是目前这种状况。从各方面的条件来讲,四川出好作品好作家的可能性很大,但这好像还只是一个期许、一个愿望。还有一件事情更令人沮丧。就是一些真正写作的人,却疏离于作协这个机构。原因自然很多。作协一些工作人员从事于文学工作,但本身对文学没有热爱,既缺乏服务热情,又没有与作家们展开文学对话的能力,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或者是最重要的原因。”这段话说到文学生态,当然也包括新诗生态,实在引人深思。
第二,新诗的评价模式亟需改变。目前有学院派、作协派、媒体派、草根派四类诗评人员,但是队伍不整,中青年骨干尤其匮乏。诗坛名宿大多老了,除却清谈几声,并无精力发现新人,提携后辈,或者真刀真枪上阵,做出几首像模像样的经典来。自新世纪网络诗歌崛起后,诗评更是严重失语。读者在网络上的即时点评,要么流于简单,要么过于随意,批评声音不大,社会反应不热烈,完全得不到诗评家们的关注和引导,也无形中抑制了新诗的发展。诗评理念也须与时俱进。肯定主流,呵护草根,提携新人,奖掖新作,是基本态度。重点解决储备不够、研究不够、前瞻不够的问题。如果能变马后炮为马前卒,相信更能切准新诗的脉搏。诗评家们也须传帮带,道理再简单不过,弟子不必不如师,雏凤清于老凤声。新诗下一个百年究竟怎样发展,诗评家的笔杆子责任很大。
第三,还有一个诗人的收入问题。草根诗人羞于谈论收入,这与主流诗坛长期以来的引导有关。有人站着说话不腰疼:写诗切忌急功近利,要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可是清贫并不是草根诗人的专利。写诗也是一门职业,求生存,保饭碗,谋生计的手段。如果一个可怜的诗人,整日吟诗作赋,半夜想吃一碗面而不得,饿着肚子岂能作出好诗来!在我们这个时代,诗人穷困潦倒就是时代的悲哀。因此草根诗人也要讲成功学。吃饱饭才是硬道理!由此说来,诗人专业化,创作职业化,作品市场化,将是新诗下一个百年的不二选择。
三、人人心中都有一首诗 伴随着网络化普及,新诗早已天翻地覆
伴随着网络化普及,新诗早已天翻地覆。全球化,地球村,世界是平的,小小寰球正在变成一个人人可以把玩的“地球仪”。电脑手机,随时随地轻松链接诗歌天下。百年新诗再出发,网络草根已崛起,小圈子变成大生态,人人心中都有一首诗。新诗民主化时代款款而来,伟大的作品、伟大的诗人化茧成蝶,呼之欲出。可以预言,伟大的作品和伟大的诗人,将来一定来自网络。
草根诗人谁不渴望远方的功名?诗人的功名就是写出一首好诗,成为一个好诗人。写诗最需要自由创作精神。从草根一跃而为主流,或许一首好诗就够了,及至永垂不朽。新百年,新生态,生活给你感觉,积淀,素材,经历给你磨难,灵感,智慧,好诗借助各种机缘,借助某一个人某一时刻的灵光乍现,会突然喷薄而出。应该说网络铺就了一条通往自由的创作捷径,接下来就是静静期待。新诗刚刚走过第一个百年,大放光芒可遇不可求,但是已经为时不远。
时代变迁,诗歌演变,人人预感到伟大的诗歌时代即将到来。主流与草根,对于新诗的题材选择,萝卜白菜,各有所爱,甚至存在巨大分歧。新诗应彰显个人好恶,还是大众精神?乃至时代,社会,国家,世界,人类,未来?诗性即人性,诗情即世情,诗意即民意。不管主流或草根,诗人应更多扎根于时代,扎根于民众,扎根于汉语,反映大众情怀和人类关切。新诗目前的不足就在于缺失与外在世界的联系,过于沉湎自我。“新诗一定程度上把自己边缘化了,因为诗人们没有大声音、大境界、大作品来唤醒民众对诗歌的注意。”(谢冕)毫无疑问,新诗应是一种构建,一种自觉,一种创造。然而,目前仍有大量的新诗写作,停留在“卿卿我我”的氛围之中,而无法进入真正的经典创造。
可以称之为经典的新诗,到底是思想性(诗意)高于艺术性(诗艺),还是艺术性(诗艺)高于思想性(诗意)?这是一对天生的矛盾。反正能让大众满意的自然会是好诗,否则读者不会买账。诗是酒,却非酒,而是酒香。诗是花,却非花,而是花香。酒香和花香给人的都是一种感觉,一见如故的,一见难忘的,一见钟情的,一见倾心的。能让人们爱上“你”,“你”就风华绝代。
显而易见,创出经典才是草根走向主流的必由之路。中国古代有悠久的诗歌历史,有丰富的诗学形态,有光耀古今的诗歌大师,有百读不厌的诗歌名篇,新诗可吸收古体诗的精华,将古典诗境与当下情绪结合起来。新诗也可吸收外国诗的精华,乃至散文、小说、音乐等等所有人类精神财富的精华,融会贯通,为我所用,既自由创作,又自我规范,集大成者,出大作品。新诗没有传统非传统之分,更没有主流非主流之分,只有起步早晚之分,经典与否之分,甚至难以分出高下。所谓经典,都是诗人们在创业实践过程中逐渐产生的。“音乐性与节奏感是新诗要守住的一条红线”,思想和情感的独创性表达更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审美追求。一首一首写出来,匠心独运,喜闻乐见,大浪淘沙始到金。
如果说音乐是有性格和色彩的,那么作为音乐的主体——歌词(新诗的另外一种形式),也是新诗创作应该重视和借鉴的。遗憾的是现在洋洋大观的新诗,赶不上几首经典的歌词。胡适的《希望》,远不及一首《兰花草》,十首“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也比不上一首“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可是人们在谈论新诗的韵律和节奏时,常常忘了提及歌词。新诗赶不上流行音乐,着实让诗人们汗颜。竟然还有人对鲍勃•迪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惊诧莫名。
新诗蹒跚走向艰辛而漫长的经典化征程。一部诗作被称为“经典”,与其说需要经过时间的洗礼和历史的沉淀,不如说这是一场新诗场域内各个话语权主体抗衡和搏杀的持久战。草根诗人正走在成名成家的路上,尤其需要得到作为主流之一的诗评家们的持久关注和激发。诗人发自内心的创新意识和创作成果,蝶变演化,与当下的文化语境,诗歌语境,批评语境相结合,新诗的语言,句式,意象,意境,音韵,节奏,完全可以嬗变到让人心动,心悦,心灵共鸣。
现在是孕育新诗的最好时代。中国梦时代,人与自然走向矛盾对立的时代,人类与科技既依赖又博弈的时代,赋予诗人绝佳的创作机遇。人们对过去的怀念和依恋,对未来的向往和恐惧,有写不完的诗歌题材。诗人们要么赞,要么劝,望闻问切,记录描摹,正可产生伟大的荷马史诗,伟大的唐诗宋词。
百年新诗走到今天,网络诗歌大量涌现,几乎人人都会写诗。作者、读者、编者、评者、爱好者,新诗人口暴涨。随着老一代慢慢故去,新一代人人都有手机电脑,人人都会上网,人人心中都有一首属于自己的诗。人人有诗的时代正在来临或者说已经来临。至少他们笔下无,心中有。诗歌的民主化时代来了,浩浩荡荡,势不可挡。人们心底的那首诗,要么你来触碰,要么自我燃烧。那些草根诗人们,必将争先恐后开出五彩缤纷的小花。而这些小花之中,必有几朵格外令人赏心悦目,格外令人流连忘返,光耀诗坛,彷如天作。(本文落笔至此,还有一条至关重要的创作理念意欲厘清:关于“我手写我心与我手写民心”,限于篇幅不再赘述。请参看笔者外一篇《高盛创业小说创作谈》)
回首新诗百年,诗坛百感交集。第一,回首百年,新诗高峰叠翠,其中不乏众多经典之作。第二,中国新诗百年发展史,其实就是一代又一代诗人从草根走向主流的蝶变成长史。第三,随着网络化,新诗民主化时代正在或者已经到来,人人心中都有一首诗,伟大的作品、伟大的诗人化茧成蝶,呼之欲出。
一、致敬中国新诗百年 百年新诗发轫于五四新文化运动
百年新诗发轫于五四新文化运动。1917年2月《新青年》刊出胡适的《白话诗八首》,被公认为中国新诗的起点。“两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从遥远的古体诗时代一下子飞到了白话诗的新时代。1920年胡适出版《尝试集》,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诗集诞生。不过真正让后人记住的不是这首《蝴蝶》,而是另外一首《希望》,后来由诗而歌改名为《兰花草》,经由台湾青春小歌后卓依婷深情演绎,流传甚广。普罗大众这才知晓原来胡适为中国新诗的开端。
后来又有人提出不同意见,说中国新诗的开端和起点不是胡适而是鲁迅。并举鲁迅的《野草》开篇《秋夜》的第一句:“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二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以为佐证。说如此分裂与重复的句法才更像一首新诗。这纯属个人之见。其中大约隐含着对胡适新诗的失望。
至此,百年新诗大体可分为五个时间段:新文化运动启蒙期、建国前后的革命英雄主义浪漫期、文革后的朦胧苏醒期、80-90年代的诗歌狂热期、及至新世纪前后绵延至今的草根网络期。无论是文化启蒙,讴歌革命,关注时代主题还是注重个人感受,新诗高峰迭起,一波又一波,优秀诗人和优秀作品不断涌现,汇成浩瀚壮观而又不免泥沙俱下的新诗海洋,引起文学界一阵阵感叹。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欧洲文艺复兴何其相似,或者说原本就有西学东渐的基因,批判社会的种种腐朽,呼唤人性的自由解放,鼓动民众顺应时代变革,用光明驱除一切黑暗。这一时期以胡适为开端,以郭沫若为代表,还有追捧徐志摩爱情诗的另一部分人,以及丁玲的小思绪,充当了新诗启蒙的先行者。
郭沫若的《凤凰涅槃》,激情澎湃,斗志昂扬,极富批判思想和启蒙意识,彰显强烈的革新精神,“凤和凰的死期将近了”,可是他们宁愿死去,也要选择涅槃重生,可以说为旧时代敲响了丧钟,为新时代吹起了号角。
民主战士闻一多,倡导新诗格律化,主张“戴着镣铐跳舞”,让新诗不失音乐之美。其代表作《七子之歌》,忧患重重;另一首《死水》,皆因“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诗人拍案而起,为民主殉难。
新月派徐志摩,一生为爱痴狂。《沙扬娜拉》,“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再别康桥》,“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掀起波光潋滟,激起心绪涟漪,甚或波澜,仿佛恋爱中的徐志摩喃喃私语,关于陆小曼,关于林徽因,关于其诗背后的爱情故事,成为后人津津乐道的话题。可惜诗人因飞机失事而英年早逝,人间最美四月天,转眼花落流水去,让人扼腕叹息,期待不了一个圆满的结局。
正如寂寞又彷徨的戴望舒,迷茫苦闷找不到出路的知识分子,《雨巷》,《我的记忆》,开启了现代诗派,诗人却沦落为寂寞暗夜的太息者和哀怨人。
丁玲的《繁星》、《春水》,一扫阴郁之气,句式短小,灵光乍现,粗看不成体制,细读充满火花,还真如天上的繁星,一闪一闪亮晶晶,又像解冻的春水,叮叮咚咚,让人情思环绕,怦然心动,自成一片天地。这种泰戈尔似的奇妙短章,也告诉着后人作诗其实也并非什么难事,绝非难上加难,只须敢于提笔,捕捉一个个灵感而已。就像小时候在夏夜里追逐萤火虫,只要敢于动手去抓总会有一番收获的。我们称之为丁玲的小思绪,正是形象得恰如其分。
国共内战及延安抗战时期,光未然的《黄河大合唱》、田汉的《义勇军进行曲》,尤其是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我深爱这土地》,语调铿锵,笔力雄浑,讴歌时代,汪洋恣肆,有一种独特的散文之美。臧克家,号称泥土诗人,善于抒写农村题材,笃定生活是诗的土壤。贺敬之《回延安》,融合了陕北民歌信天游的形式,语言质朴,生活气息浓厚,感情炽热,极富音乐之美。这一时期的革命浪漫主义诗歌,工农兵题材,抗战主题,英雄精神,代表着最广泛的四万万同胞的呼声和共同命运,是那个时代轰轰烈烈的大音希声。
总体来看,从白话诗诞生,至新中国成立,若论新诗之最高成就者,还属毛泽东无疑。不论从其领导地位,文艺思想,诗歌成就,时代影响来说,都是当之无愧的。唯其一点,毛诗皆为古体,似乎称不上“新诗”。然而“新诗”之所以为新诗者,并不完全拘泥于古体或自由体,文言或白话。应该说新时代的人所作的新时代的诗,今天的人所写的今天的诗,皆可归位于“新诗”。
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不但开创革命诗派(应该说对革命诗歌有重大影响,点燃了一把大火,其诗言志,抒情,写景,状物,催人奋进,令人向往),更有领袖群伦、舍我其谁之气概,之气魄,之气势,之气度。也难怪蒋介石发动全党全国之力,欲与天公试比高,然无人有此雄壮之心,无人有此博大之心胸和襟怀,纵是想破了脑袋也枉然。
其后改革开放,80年代诗歌狂潮,朦胧诗异军突起。然而斯时的朦胧诗终归是有些“朦胧”,大多晦涩,不顺畅,情绪灰色,让人直呼看不懂。大约都是中了西方诗的流毒。穆旦等人的翻译诗就有这种毛病。象征寓意驳杂,极不适合国人口味。卞之琳是个意外,他一心追求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一生作诗不过五千余言,算得上一个字斟句酌、惜墨如金的苦吟诗人。其《断章》:“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堪称新诗锤炼字句的绝佳典范。
大约同一时代的台湾新诗,余光中、郑愁予、洛夫等人,强调“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然而他们最后都回归了传统。余光中后来更是宣称“我的血脉中有一条黄河的支流”,此生“要做屈原和李白的传人”,其代表作《乡愁》哪里还看得见西方诗的影子?完全是古典的音乐诗,情深意长,音韵动人。
这一时期的代表性诗人,北岛,顾城,以斗士姿态走上诗坛,又随之淹没于汪洋大海。原本艰难曲折的生动故事,却酿成难以谅解的人生事故。北岛的那首《回答》:“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道出了一个有着极重自卑感的斗士内心踯躅的英雄情结,可是漂泊流浪的心却再也回不去。顾城的那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因其不健全的人格而诗格自然被遗忘殆尽。偶有论者为其发声,真不知其意何谓。
朦胧诗的真正代表,当属席慕容和舒婷。细看舒婷之诗,说朦胧其实并不朦胧,同时代的年轻人大多还是能会其意的。虽有多种解读,大意应该不会错也不太差的。《双桅船》,《致橡树》,风靡一时,并非晦涩到让人读不懂,乃至产生误解或曲解。倒是同时代其他更多的诗人,走入了朦胧诗晦涩的死胡同。
某些朦胧诗晦涩到让人看不懂,约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有意为之,所谓曲意难解,说白了就是不愿与你凡夫俗子为伍。另一种是无意为之,说白了就是思想还不够捋顺,意象还不够鲜明,表达还不够到位,心里也想说的明白点,可是诗做出来不是想象中的样子。自己一本糊涂账,大众自然不买账。
接下来有一位诗人,号称“北大三杰”的海子,在此须要提一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多么美好的理想,多么美好的憧憬,多么美好的咏叹!可惜诗人总是缺什么写什么,心中怎么渴望嘴里怎么呼喊。海子终其一生并未遇见春暖花开,临终也不是面朝大海,而是选择了一处关隘。山海关,天下第一关,真是颇具新诗的意境和象征。面对关隘,相信海子内心也彷徨过,犹豫过,忐忑过,可他向往不了戴望舒的雨巷,尚有油纸伞,尚有丁香花,尚有撑着油纸伞像丁香花一样的姑娘。海子面对的是关,这个关生死重重,到底该过该留,该进该退,该生该死,挣扎,纠结,绝望!最后海子以死成就了一首悲怆的诗!
学院派诗人王家新,西川,欧阳江河,臧棣等,因崇尚西方现代主义而走向先锋探索,其诗颇多意象和象征,后来也有适度口语化。大约是学养太深,他们的诗如佛,如道,如理,凡人一般参不透,因此也就少有人去参、去悟、去透。大约他们写诗的时候也没想着让太多人看明白,惟愿在小圈子里流传。正因为看不懂,普罗大众也就不想看,不去看,不看白不看,看了也白看。譬如西川,复杂的思想,含混的意识,驳杂的散文化倾向,各种不确定性包罗万象,什么意思都有,具体什么意思一般无人知晓也无从知晓,只有去猜。把诗写到这种技术层面着实令后人仰视。王家新的诗更纯净一些,也更纯粹一些。
然而诗不就是给人看的么?难道只给心仪的师友们看?诗还须反映普通人的情感,普通人的遭遇,普通人的梦想。通俗易懂的,大众喜爱的,脍炙人口的,才能流传下来,流传开来。诗歌界曾有一段公案,证明笔者所言非虚。
有很多人非常看不起那个掀起过诗歌风暴的汪国真。欧阳江河曾说:汪国真的诗全都是“假诗”,汪诗对中国当代诗歌唯一的作用就是阻碍,对学生是一种毒害,是一种“恶趣味”,羞于被称为汪国真同一时代、使用同一语言的诗人。更有甚者,说汪诗是“生命能够承重之轻”,是文化贫瘠的反映,直斥汪诗为垃圾,为手纸,为小儿科,为不入流。这些话恶劣到极致。不过有一点歪打正着说对了:今后写诗还真就像吃喝拉撒睡,绝不是什么神秘莫测的事。
毋庸讳言,欧阳老师他们的学术精神无疑是值得尊敬的,可是他们评论汪诗的这些话却显得极为可疑。就像中国房市的专家,股市的大咖,总也号不准房市或股市的脉。我们的意思是说,他自己却并没有哪怕一首可称之为经典的诗让人记住他。亦无特别出色的作品引领风尚。就像汪诗《年轻的潮》一样。
汪国真的诗歌简短而寓意明晰, 昂扬而又超脱,清新的笔法和细腻的感情比之前的“朦胧诗”更浅吟低唱,更通俗易懂,20多年来一直倍受青年人喜爱,就是对中年人也有很大激励作用。笔者身边至今还有不少人以汪诗的名言警句为座右铭。其诗集销量总版印数超过600万册。说他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似乎一点也不为过。“汪国真现象”为时代创造了大量的读者、作者和诗歌爱好者。“汪国真热”称得上那个时代经典的文化符号之一。此后的余秋雨,于丹,易中天,直到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也许还有韩寒,郭敬明,余秀华,网络文学IP热,都要稍逊一筹,没人达到汪国真的热度。或许唯有“超女”可比。
然而却有太多的“他们”看不起他。当今诗歌某种程度上被边缘化了,用汪国真的话说,“观众已经走光了,演员还在台上装腔作势”。“他们”这些人对新诗一定程度上的边缘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第一,你没有比别人更高明,写出一批质量口碑俱佳的作品来;第二,你走入了小圈子,也根本没有口传心授,用过硬的作品教育读者怎样去读诗,怎样去作诗;第三,你看不起汪国真不就是看不起广大的年轻读者么?现在追看“中国诗词大会”的,有几个不是当年汪诗的粉丝或者汪诗的粉丝的下一代?毛主席曾说熊向晖一个人能抵三个师。依笔者所见,汪国真对新诗的普及贡献,抵得上“他们”所有的一大群人。
很遗憾没人接下汪国真的棒。“现在的读者不是不喜欢诗,而是不喜欢那些装腔作势的诗”。“深刻的、崇高的、有水准的 ”诗歌,看来还是用浅显易懂的汉语表述出来为最好。都说青年是祖国的未来,可是对青年的喜爱你却不赞同,甚至批评抨击,岂非自相矛盾,一味站在个人的立场说话?俞伯牙和钟子期,高山流水遇知音,子期病逝,伯牙摔琴,知音不再,弦断有谁听?其实俞伯牙那首曲子,凡人也是能够听懂的,钟子期不就是一个樵夫嘛!《高山流水》至今满大街流传,几乎人人耳熟能详。当年伯牙毁琴烧谱,成就一段曲终人散的佳话,盖因慕名清高不肯“同流合污”者也。今人还有谁欲东施效颦耶!
接下来可谓新诗的群星闪耀时刻。一大批卓有成效的诗人,写出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口语化新诗。他们各有所长,各有风格,各有代表性群体,各有自己赖以成名的代表作,目前都已走上诗坛主流地位,领导或主导着一席之地。他们经过艰难摸索,经历过崇拜洋诗的先锋时代,又逐渐回归到中国古典诗词文化里去寻找和汲取营养。以笔者有限的视野和观察,特选取几个尚在主流圈层的大门内外徘徊的草根诗人,我们姑且称之为后起之秀,做一简单探讨。
譬如扎根于彩云之南的雷平阳,珠三角的打工诗人郑小琼,长三角台州湾的柯健君,山西太行山的勘探诗人张二棍,中部已然崛起然而始终摇摇晃晃的余秀华。也不妨提一提刚刚开始步入诗坛的创业诗人高盛。
雷平阳出名早,评论其诗者大有人在,读者皆为其云南特色着迷。柯健君位于浙江台州,笔者与其并无深交,因为一次全国性的诗文笔会结识于天台山,然其所赠之诗集逐一浏览拜读过,尤喜他《在海边》的一系列吟唱。
在此想着重说说郑小琼。郑小琼的打工诗,像“五金厂的铁一样冰冷”,然而却自有温度。数千万打工仔打工妹,比之全国的中学生大学生,群体也不算为小。打工者的经历,经验,故事,心事,情绪,表情,理想,梦想,喜怒哀乐,嬉笑怒骂,有太多的角度可以入诗,多少个黄麻岭也载不动,装不下。然而郑小琼步入诗坛红起来也有好多个年头了,诗集也出了十多本了,却一直没能大红大紫,虽有一方话语权,终因学历、见识、思考之短板,并未迈入真正的主流(或者郑小琼是主流的,笔者这样说并无任何恶意,更多的是抱憾和反思)。
写诗最关键看发轫期和成熟期。郑小琼在发轫期获得追捧,在成熟期相对来说受到主流诗坛的关注度不够。囿于一隅摸着石头过河。郑小琼的诗歌,缺失进一步深挖的自觉,缺失为打工群体代言的担当胸怀,缺失主流诗坛的专家会诊,而这些主流专家特别是作协的专家们是有这个义务的。主流诗坛的关注和帮扶不够,而且总是滞后,一首歌已唱完了,捧哏还没登场。留作盖棺定论耶?正确的做法是研讨之,剖析之,助推之,方可经典化,竖起新诗的丰碑。
郑小琼的诗歌若能站在打工者角度,描摹抒写之外,更多社会学思考,成为打工一族真正的代言人,流传必定更广,社会影响必定更大,也必定更能接近新诗皇冠上的明珠。推而广之,在我们这个时代,伟大的诗人,伟大的作品,常常就是这样擦肩而过或者偃旗息鼓的。如果主流诗坛不能提前发现基层的苗头与动态,并辅之以无微不至的培育和关怀,我们终将剩下空空的叹息。
余秀华的诗歌赤裸,坦率,突破框框,毫无顾忌,颇多出格之语,借此走红诗坛。有人谩骂她的诗大部分都是艳诗,甚至是“荡妇体”。余秀华毫不在乎,“荡妇就荡妇”,更显出诗人的可贵与坚守。愚以为余秀华出名,草根的同情多于主流的赞赏。然此非主因,顶多算一偏门,但绝不是意外。余秀华诗歌提振人心的精神,在于她拖着一身病躯坚持发出自己的声音!那首最引人注目也最让人诟病的《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其实写的很好。那个“睡”字如果换成一个“爱”字,有何不可?一个“爱”见怪不怪,一个“睡”惊世骇俗,石破天惊!诗人宁愿出此下策,冒着毁灭自己的风险,也要博取主流诗坛“赞赏少于同情”的关注。如此艰辛的成名之路,想当年贾平凹,陈忠实都碰到过,命运何其相似乃尔!这种故事将来还会不断上演。福兮祸兮?幸与不幸耶?
自诩“看破中国式创业,领教中国式商道”的创业诗人高盛,前半生执着于创业,人到中年心血来潮步入诗坛,原本虾兵蟹将一个,欲在前人不曾跋涉的创业领域开辟一隅,以期写出言之有物、有血有肉的新诗来。“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梦叫中国梦,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诗叫创业诗。给创业一点诗意,无论得意还是失意”。然其功力尚浅,浅尝辄止,自知诗才有限,不如专攻小说一途,探索做创业文学,美其名曰创业小说,志不在小。此路能否走通尚有九九八十一难,十万八千里行程,就看能否习得孙猴子的筋斗云,暂且不提也罢。
二、何为主流?何为草根?不管从作者、读者、评者哪个角度看,百年新诗都是蔚为壮观的
不管从作者、读者、评者哪个角度看,百年新诗都是蔚为壮观的。中国新诗百年发展史,其实就是一部草根诗人走向主流的蝶变成长史。
何为主流?何为草根?所谓主流与草根之称谓,实属强加于人的一种勉强。正如太极之阴阳,手掌之两面,彼此彼此,互为依存,而绝难割裂开来。主流都是从草根一步一步崛起的,崛起之前的主流谁没做过草根?现在的问题是,随着网络诗歌的快速崛起,主流压不住草根,草根却很有颠覆主流之势。
所谓主流,第一身处主流,居于主要城市,身为主流人群(作协派,学院派,媒体派),处于庙堂之高,而非江湖之远;第二拥有一方主流阵地(报刊,出版,评论,网络),主流渠道(纸媒,电媒,网媒,教科书),哪怕一个小小的区域,小小的平台,小小的阵地,最关键的手中有笔,可判生死,府中有粮,饿不着冻不着;第三开口必为主流话语,以期发出主流声音,凤凰来仪,流播四方,百鸟朝凤,万国朝贡。除此之外,其他的大抵都算作非主流的草根派。
所谓草根者,非主流也。非茎非叶,非花非果,不过草芥之末。荒野田边,河坡沟岸,偏僻蹊径,砖石墙角,野蛮生长,比比皆是。当春破土而出,临冬枯萎入泥。盛时疾风劲吹,败时零落凋蔽。白居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说的是草根。然笔者所言之草根,并非原上之根深叶茂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有草葳蕤而为草原,绝非一般草根。真正的草根,往往是土生土长的,自生自灭的,偶尔开一小花,装饰门面,点缀天涯,并不夺人光辉。
草根乃未名之末者,人微言轻,既非作协名家,亦非学院名师,更非媒体代言人,自诩草根者大多懂得夹起尾巴做人,有时心血来潮大约也作诗。
我们今天所说的草根,更多的是一种譬喻。喻为散落于民间的草根诗人。正常情况下草根诗人躲藏遮掩犹未不及,何敢曝光于众目睽睽之下侃侃而谈?皆因当今网络科技之发达。草根一派不同于主流诗人,整天穿梭于各种会场、酒场脱不开身。草根诗人身为草根,自然而然倾心于为草根写诗,他们一般热衷于网络媒体(论坛,博客,微博,微信,QQ,APP,朋友圈),因为他们实在也没有其他的地方可去。其他地方都是主流诗人的天下。幸得网络气氛也很热烈,整天里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交流切磋,刷存在感,不服就放马过来比试,生动活泼比主流还主流,也因此草根的根须可以绵延不断,不致于倒地萎顿。
现在主流诗坛多忧虑新诗越来越边缘化了,草根诗人们却说新诗早已“赶唐超宋”。君不见网络诗歌有增无减,热度正酣,何来边缘化、小众化、消失论之担忧?中国历史上有哪个朝代让文学特别是诗歌这样繁荣过?曝光过?没有!只有今天!多少学文的,不是学文的,都对诗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写诗,读诗,爱诗,正在成为一种时代风尚。种子已埋下,有苗不愁长。
当然,网络上的草根诗人,无论其人还是其诗,注水的成分也不少。新诗气短,好作品缺失,经典化稀有,诗作虽以海量计,大众公认的好诗却没有几首。广泛传播开来的更是少之又少。诗歌之美,美在遣词造句,美在韵律节奏,美在赏心悦目的外观形式,更美在语言文字背后的诗人的心。经典的,口语的,千锤百炼的,野蛮生长的,有文化担当的,侧重于娱乐的,都可有好诗。
人们对新诗诘难,本质上还是对草根的蔑视,不屑,不尊重。人们总是习惯于站在一种看似“主流”的立场来批判新诗,殊不知新诗从一开始出生就是个草根派,至今也仍然是。虽然诗坛上有大把的所谓“主流诗人”。远的千年前,李白是个放逐者,杜甫是个落魄者,孟浩然是个隐居者,李商隐是个失意者,他们都不曾贵为主流,顶多算个门客,主流之光,昙花一现。近的百年前,胡适、郭沫若,哪个不是不折不扣的草根派?因为那时还是古体诗的天下。
中国新文学史上,鲁迅、巴金、老舍等名家,他们当时都是社会上并非主流的一小撮人,起初的创作道路都走得很艰辛,都是在各种质疑和争议中从草根步入主流的。鲁迅是弃医从文的,巴金是学外文的,老舍是大杂院出来的,后来的莫言,余华,阿来,严格来说皆非科班出生,最多算得上半路出家,他们都是一辈子自己教自己,完全靠自学,然而他们最后都成为“天生的作家”,成为天生为写作而生的人,成为中国文学界的中流砥柱乃至旗帜。
新时代的诗人中汪国真很有代表性。当年《诗刊》的编辑唐晓渡曾回忆说,“汪国真的诗,九个编辑里没一个重视的。”即便在后来“汪国真热”席卷全国之后,“主流”文学刊物仍然拒绝刊发汪国真的诗作,主流文学界对汪诗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冷漠,诗评家们也大都保持沉默。慧眼不识珠,伯乐不相马,扶植新人成为一句令人啼笑皆非的空话。那些孤芳自赏的所谓主流,在“汪国真热”普及新诗的过程中沾尽了风光,从而确立了自己牢固的诗坛主流地位。
汪诗被嘲笑,挖苦,贬低,不予重视,褒少贬多,与读者反馈和市场反应截然相反。“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我微笑着走向生活”,却并没有几个主流诗人吟得出。这正说明汪诗与时代保持着与时俱进,而主流们却日渐疏远了自己的核心客户群。汪诗的社会影响力被严重低估了。其所起的作用或许是莫言都无法替代的。汪国真进入主流诗歌史天经地义,这个里程碑式的记忆,任谁想抹杀也抹杀不了。
那些看不起汪诗的同行,我们不妨称之为文化诗人。他们大都把诗当作文化的载体,一生坚持与诗对话,他们的智商是超级的,知识是渊博的,学养是深厚的,然而他们并不是活蹦乱跳的、烟熏火燎的、知冷知热的诗人。他们大约从小考、中考、高考一路过关斩将,学士、硕士、博士一路领先同侪,讲师、教授、博导一生顺遂无虞,没有名落孙山的揪心,没有饥寒交迫的窘境,没有弹尽粮绝的考验,书香茂盛而生活贫瘠,他们的生活就是书,书就是生活,没有基层打拼的生死体验,当然也就写不出大众喜爱的诗来。他们虽然能感受和预知,然而却难以体验某种刻骨铭心的热爱或者痛苦。当然这不是他们的错。
因此,他们写诗其实就是论诗,多理性,多思辨,继承了朱熹的衣钵,擅长于教诲、品评和堆砌,唯独少了草根的生态和草香的味道。他们的诗肯定侧重于诗艺,说白了就是炫技。晦涩的太晦涩,浅白的不屑为。然而,赋比兴比不过诗经,意识流比不过楚辞,善用典比不过杜甫,格律精准比不过唐诗,音乐传唱比不过宋词,轻松活泼比不过元曲,正如李太白登黄鹤楼时所感叹: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李太白的诗天然去雕饰,他们更是学不来的。
主流们正确的做法是融入草根,老老实实承认自己从前也是个草根,谁并不比谁高明多少,关注他,接纳他,包容他,直至融入其中,同呼吸共命运,身先士卒,做出表率,写出一批有号召力、有影响力的作品来,扶持基层草根创作,践行传帮带三部曲,提前发现,深入挖掘,引导之,成熟之,共同推动新诗向下一个百年发展。张艺谋,莫言,余华,当年也是没人愿意荐之,无奈只得出口转内销,落得一个专门揭露国人阴暗面的礼帽。作品还是那个作品,有人开始言必称之,鞍前马后扶之坐庄。批判的是那批人,追捧的还是那批人。这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墙内开花墙外香的事,真不希望看到在家门口轮番上演。
主流们内部也常常有不同的声音。有褒奖的,有质疑的,有拥护的,有反对的,有时会吵得很激烈,针锋相对,相互掐架。譬如对新诗的开创者胡适,有些人奉若神明,有些人不以为然,有些人就很看不起。不过这些人品评新诗臧否人物,面子上惊涛骇浪,里子上轻描淡写,激不起什么醒目的水花。
纷纷扰扰的新诗纷争,归根结底是话语权之争。格律体自由体之争,中国诗外国诗之争,主流派草根派之争,谁主谁次,孰优孰劣,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诗人说诗人有理,读者说读者有理,纷纷攘攘,莫衷一是,千姿百态,不足为怪。说白了都是话语权之争。作者,读者,编者,评者,各有各自的立场,各有各自的圈子,各有各自的利益,人人都想当老大,让别人服从自己的意志,但总缺少当老大的风范。老大要么扶持人,要么发现人,要么领导人,要么服务人,可是这种瞻前顾后乐相马、俯首甘当孺子牛的老大到现在还没出现。
其实,遵从格律是好诗,自由洒脱也是好诗;西洋诗意象优美,中国诗意境更美;主流诗人写得一首好诗,草根诗人偶尔也有上佳的发挥。格律并非好诗的唯一标准,语言也并非好诗的唯一标准,好诗的唯一标准是诗意,诗人心底的诗意,读者读到的诗意,二者缺一不可,缺一不成其为诗意。新诗诗意之美,可大可小,可远可近,可内可外,可虚可实,亦明亦暗,亦正亦邪,天地环宇,包罗万象,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诗意之美,正如百舸争流,百花争艳,百鸟争鸣,可以极大地满足诗者、读者、编者、评者的各自审美。
然而诗意并非诗艺。新诗要表达大众理想还是个人理想?新诗要走入大众化还是小圈子?新诗要走入更加广阔的空间还是死胡同?这不是一个选择题,也不是一个填空题,而是一个权衡兼顾的论述题。无论现实主义还是浪漫主义,无论主流诗人还是草根诗人,一首新诗问世,其诗意或诗艺的强弱好坏,唯一的裁判是读者,而不是诗人自己。一个诗人无权评判自己的作品,正如一个人不能左右自己的命运。你的诗意好,读者有感觉;你的诗艺好,读者有感受,二者必居其一。如果诗意或诗艺并未捂热,读者毫无体验,任你孤芳自赏,敝帚自珍,读者现在看不懂,将来也不会看。你的付出只能默默压在箱子底。
虽然诗意并非诗艺,但是诗人的诗意却要借重于诗人的诗艺得到自由任性的发挥。李白的诗意好,“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一读就能感觉到。贾岛的诗艺好,埋头琢磨“僧敲月下门”还是“僧推月下门”,结果冲撞了韩愈的仪仗,也因而有了“推敲”之佳话。杜甫诗意与诗艺俱佳,“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让人叹为观止。
诗意可捕捉,诗艺可修炼,当今看不明白的诗歌生态更让人担忧。新诗已被逼上全面深化改革的风口浪尖。若不伤筋动骨,肯定收效甚微。绝非巡视整改就可轻易收兵。第一,新诗的产出模式不妨借鉴供给侧改革。主流诗人既有阵地,草根诗人网络平台,顺其自然还是弥合边界?鼓励发展还是横加阻拦?质疑诘难还是容错纠偏?放开数量还是锤炼质量?看起来涉及主流非主流话语权之争,其实显现了体制机制之利弊。新诗盘子已经很大了,体制机制几十年不变,主流诗人有垄断之弊(最为诟病的是小圈子生态,新诗发表和出版主要看谁的脸熟),草根诗人有拼凑之嫌(主要存在粗制滥造、急功近利等毛病),根深蒂固,难以撼动。供给侧改革的妙处,在于淘汰落后产能,扶持有创新活力的经典品牌。作为新诗最大产出量的主流派和草根派,按图索骥不难药到病除。
四川省作协主席阿来的一段话或许很有代表性:“四川人口多,写作资源很丰富,四川的文学不应该是目前这种状况。从各方面的条件来讲,四川出好作品好作家的可能性很大,但这好像还只是一个期许、一个愿望。还有一件事情更令人沮丧。就是一些真正写作的人,却疏离于作协这个机构。原因自然很多。作协一些工作人员从事于文学工作,但本身对文学没有热爱,既缺乏服务热情,又没有与作家们展开文学对话的能力,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或者是最重要的原因。”这段话说到文学生态,当然也包括新诗生态,实在引人深思。
第二,新诗的评价模式亟需改变。目前有学院派、作协派、媒体派、草根派四类诗评人员,但是队伍不整,中青年骨干尤其匮乏。诗坛名宿大多老了,除却清谈几声,并无精力发现新人,提携后辈,或者真刀真枪上阵,做出几首像模像样的经典来。自新世纪网络诗歌崛起后,诗评更是严重失语。读者在网络上的即时点评,要么流于简单,要么过于随意,批评声音不大,社会反应不热烈,完全得不到诗评家们的关注和引导,也无形中抑制了新诗的发展。诗评理念也须与时俱进。肯定主流,呵护草根,提携新人,奖掖新作,是基本态度。重点解决储备不够、研究不够、前瞻不够的问题。如果能变马后炮为马前卒,相信更能切准新诗的脉搏。诗评家们也须传帮带,道理再简单不过,弟子不必不如师,雏凤清于老凤声。新诗下一个百年究竟怎样发展,诗评家的笔杆子责任很大。
第三,还有一个诗人的收入问题。草根诗人羞于谈论收入,这与主流诗坛长期以来的引导有关。有人站着说话不腰疼:写诗切忌急功近利,要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可是清贫并不是草根诗人的专利。写诗也是一门职业,求生存,保饭碗,谋生计的手段。如果一个可怜的诗人,整日吟诗作赋,半夜想吃一碗面而不得,饿着肚子岂能作出好诗来!在我们这个时代,诗人穷困潦倒就是时代的悲哀。因此草根诗人也要讲成功学。吃饱饭才是硬道理!由此说来,诗人专业化,创作职业化,作品市场化,将是新诗下一个百年的不二选择。
三、人人心中都有一首诗 伴随着网络化普及,新诗早已天翻地覆
伴随着网络化普及,新诗早已天翻地覆。全球化,地球村,世界是平的,小小寰球正在变成一个人人可以把玩的“地球仪”。电脑手机,随时随地轻松链接诗歌天下。百年新诗再出发,网络草根已崛起,小圈子变成大生态,人人心中都有一首诗。新诗民主化时代款款而来,伟大的作品、伟大的诗人化茧成蝶,呼之欲出。可以预言,伟大的作品和伟大的诗人,将来一定来自网络。
草根诗人谁不渴望远方的功名?诗人的功名就是写出一首好诗,成为一个好诗人。写诗最需要自由创作精神。从草根一跃而为主流,或许一首好诗就够了,及至永垂不朽。新百年,新生态,生活给你感觉,积淀,素材,经历给你磨难,灵感,智慧,好诗借助各种机缘,借助某一个人某一时刻的灵光乍现,会突然喷薄而出。应该说网络铺就了一条通往自由的创作捷径,接下来就是静静期待。新诗刚刚走过第一个百年,大放光芒可遇不可求,但是已经为时不远。
时代变迁,诗歌演变,人人预感到伟大的诗歌时代即将到来。主流与草根,对于新诗的题材选择,萝卜白菜,各有所爱,甚至存在巨大分歧。新诗应彰显个人好恶,还是大众精神?乃至时代,社会,国家,世界,人类,未来?诗性即人性,诗情即世情,诗意即民意。不管主流或草根,诗人应更多扎根于时代,扎根于民众,扎根于汉语,反映大众情怀和人类关切。新诗目前的不足就在于缺失与外在世界的联系,过于沉湎自我。“新诗一定程度上把自己边缘化了,因为诗人们没有大声音、大境界、大作品来唤醒民众对诗歌的注意。”(谢冕)毫无疑问,新诗应是一种构建,一种自觉,一种创造。然而,目前仍有大量的新诗写作,停留在“卿卿我我”的氛围之中,而无法进入真正的经典创造。
可以称之为经典的新诗,到底是思想性(诗意)高于艺术性(诗艺),还是艺术性(诗艺)高于思想性(诗意)?这是一对天生的矛盾。反正能让大众满意的自然会是好诗,否则读者不会买账。诗是酒,却非酒,而是酒香。诗是花,却非花,而是花香。酒香和花香给人的都是一种感觉,一见如故的,一见难忘的,一见钟情的,一见倾心的。能让人们爱上“你”,“你”就风华绝代。
显而易见,创出经典才是草根走向主流的必由之路。中国古代有悠久的诗歌历史,有丰富的诗学形态,有光耀古今的诗歌大师,有百读不厌的诗歌名篇,新诗可吸收古体诗的精华,将古典诗境与当下情绪结合起来。新诗也可吸收外国诗的精华,乃至散文、小说、音乐等等所有人类精神财富的精华,融会贯通,为我所用,既自由创作,又自我规范,集大成者,出大作品。新诗没有传统非传统之分,更没有主流非主流之分,只有起步早晚之分,经典与否之分,甚至难以分出高下。所谓经典,都是诗人们在创业实践过程中逐渐产生的。“音乐性与节奏感是新诗要守住的一条红线”,思想和情感的独创性表达更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审美追求。一首一首写出来,匠心独运,喜闻乐见,大浪淘沙始到金。
如果说音乐是有性格和色彩的,那么作为音乐的主体——歌词(新诗的另外一种形式),也是新诗创作应该重视和借鉴的。遗憾的是现在洋洋大观的新诗,赶不上几首经典的歌词。胡适的《希望》,远不及一首《兰花草》,十首“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也比不上一首“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可是人们在谈论新诗的韵律和节奏时,常常忘了提及歌词。新诗赶不上流行音乐,着实让诗人们汗颜。竟然还有人对鲍勃•迪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惊诧莫名。
新诗蹒跚走向艰辛而漫长的经典化征程。一部诗作被称为“经典”,与其说需要经过时间的洗礼和历史的沉淀,不如说这是一场新诗场域内各个话语权主体抗衡和搏杀的持久战。草根诗人正走在成名成家的路上,尤其需要得到作为主流之一的诗评家们的持久关注和激发。诗人发自内心的创新意识和创作成果,蝶变演化,与当下的文化语境,诗歌语境,批评语境相结合,新诗的语言,句式,意象,意境,音韵,节奏,完全可以嬗变到让人心动,心悦,心灵共鸣。
现在是孕育新诗的最好时代。中国梦时代,人与自然走向矛盾对立的时代,人类与科技既依赖又博弈的时代,赋予诗人绝佳的创作机遇。人们对过去的怀念和依恋,对未来的向往和恐惧,有写不完的诗歌题材。诗人们要么赞,要么劝,望闻问切,记录描摹,正可产生伟大的荷马史诗,伟大的唐诗宋词。
百年新诗走到今天,网络诗歌大量涌现,几乎人人都会写诗。作者、读者、编者、评者、爱好者,新诗人口暴涨。随着老一代慢慢故去,新一代人人都有手机电脑,人人都会上网,人人心中都有一首属于自己的诗。人人有诗的时代正在来临或者说已经来临。至少他们笔下无,心中有。诗歌的民主化时代来了,浩浩荡荡,势不可挡。人们心底的那首诗,要么你来触碰,要么自我燃烧。那些草根诗人们,必将争先恐后开出五彩缤纷的小花。而这些小花之中,必有几朵格外令人赏心悦目,格外令人流连忘返,光耀诗坛,彷如天作。(本文落笔至此,还有一条至关重要的创作理念意欲厘清:关于“我手写我心与我手写民心”,限于篇幅不再赘述。请参看笔者外一篇《高盛创业小说创作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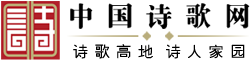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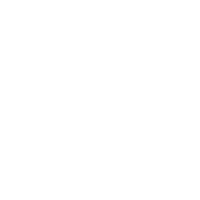

 (2次)
(2次)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34246号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34246号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