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早晨,有两条路,相差无几,
都埋在还没踏上脚印的落叶底下。
——弗罗斯特《一条未走的道路》
(11—12行)
鲜美的汁液:露万点潋滟的幻想
沉浸在树梢之精华的迷人的梦中,
——颜隼《偶像的黄昏》
(第8节6—7行)
诗总是靠诗人完成。
——帕斯《鹰还是太阳》
弹指一挥间,
此地方便是会合点,
现实的抖动和现实的颤动,
时间是一个水晶的球体
滚落到我的怀里;
沿着这条回声之路:
老鹰在上空展开墨的翅膀与尾翎
不停地盘旋,它锯一样的喙
随时准备朝地面俯冲。
既不是巨人或是大头们
在重返校园的路上。
记忆是个水潭
我的眼睛很渴:不放过
一切草木
虽然它们大多已不是过去的原样,
我的额头上至今尚未出现曙光
做为一个知识居士
又回到起点,
是赢是输
无人回答这类问题。
我服从安排,
天空少而云彩很多,
眼前就是一座石桥。
一种狂暴闪光的物质
闪烁在桥栏上
桥也不是当初的桥
不过有点相像。
天边凹陷的蔚蓝
映入我的眼帘
众人缓慢地行走
在奔向一个中心地域。
建筑物抽象的明镜
远远地就能望见
熟稔的景色于它的四周展现
多少年来不用描绘
始终在这儿
笔直耐心地像把人等待;
仿佛从这里走出去的人
都走向了迷宫岔路,
如今又回到山峦幸福的怀抱,
回到楼群幸福的韵律中。
天地间
只有在这里
才能与自己相遇:
过去的那个我正好奇地打量着我
没有疑问,也没有慰藉之语。
我的影子
正承受着诸多不真实的威胁,
然而在一种水泊似的清晰中
所有的都是那么现实。
一棵古榆树出现在桥的另一端,
接着又是
另一棵粗壮﹑黢黑的古树。
我在一双拥有记忆的眼睛的形象中
行走。我搜索每一道景物:
哪些消失了,却仍然具有幻影与反光;
空虚被步步逼退,
“品”字形楼终于会开口说话。
太阳并没有糊涂地摧毁这地方:
校园背后树木苍翠的山岗
四周散落的墨汁般的丛林,
虽然它们不再提供神话
和风的绿色的喧嚷。
在感觉和预感之间
我似乎走完了很长的一截路,
终于摸到它们的边际
以及白石灰﹑砖墙和旧时光。
站在桥上,河流在桥墩下
几乎成为一泓墨绿的静水,
处处充满着微小的奇迹;
神奇的水生植物,褐色的浮渣,
对于曾经的漫游者的光临
没有一丁点响应。
我的一只眼仍在搜寻:沙滩和草地,
河岸边供洗涤东西之用的长条形的石阶;
已不会再有发现,全都被改造
或者是被河水淹没了。
唯一列古老的河堤未变
它的故事的账目越记越多,
不在乎我的意念多于色彩
此刻我在自己身上不停地
往下落。
操场,庭院,教学楼,食堂
在一个像比时间还大的下午
全都映入眼帘。一个飞行的符号
穿越过晴朗的高空。
楼群仍是未完成的样子
楼群已是完成的样子。
几何图形的正面
朝每个人敞开着它的
大大的豁口:
中心位置上
造型端庄典雅的主楼
似在讲着人世间最亲切的方言,
一棵孤零零的似一分为二的V形大树
日夜将它守卫。奇异的命运,
该留的什么都没有被抛弃,
或许只有线形时间是一支箭。
图书馆,报刊栏,还有那些
纵横两列夹道相对称的桦树呢?
门户尚在:一一被打开,
室内的陈设早已改观,
我浏览的大部头的红色书卷
亦已灰飞烟灭
连书架都被清理一空
(一千零一夜:王子,公主
一幅幅白描的插图;
穿军官制服回乡探亲正走过幽巷的安德烈﹒保尔康斯基)。
木质楼梯换成水泥制作的梯阶,
原初教室内的木地板还在:
木板的纹路线像天象图一样
向我呈现太阳涂写和命名的字迹。
对面教室的天花顶坍塌了一角,
门被封死。太陈旧了;
有人在身后监视着我
那是与我形影不离的另一个我。
下午二点四十分。
廊柱不禁发问:你还在精神萎靡?
到此时你还没有被惊醒?
我那时的双眼朝我注视
一双十八岁时的人的眼睛
从不曾留意的各个虚空的角落,
从我曾经呆过的地方,
到处有模糊的影子和幽灵的集结。
我的眼睛既无惊讶也不同情,
时间像鸟儿洞穿过我们的身体,
或者说像子弹,是一个比喻;
肢体尚直立
尚存在:“泥土的人”,
麻木的人,外貌与身形已大大地改变。
脸上的皱纹无人破译。
无须用眼睛一直观看:过路的人
你最终看到了什么?
你来自何方?
还将回到原来的户籍地。
我对无名的东西愤慨,
却说不出无名的东西在哪儿。
忙于拍摄,一一把所有物件指点观望,
巨大而又牢固的物件也将我观望。
我的眼睛忍不住将一切景色吸纳:
大到一整片高高的屋顶,
小到别人感触不到的
空气中细细的流沙:
没有流沙,只有匆匆的时间的颗粒;
下午三点一刻钟
光亮在燃烧,
目光落入棱角分明的建筑物峥嵘的峭壁间,
回声的波浪使我的听觉具有了灵魂,
我感到很渴。胡塞尔的现象学已将我征服:
我什么也不想饮不想喝,
片片白云在头顶上方停滞,
温煦的清澈的空气
紧紧地把我们包围。
在花坛的左侧
过路的人,你来自何方?
我此刻就在当时的地方:
在一切还没有化作空气的地点
在不幸与幸运之间短暂地停留。
痕迹尚可寻觅,我所说的事物的瓦砾
也许并不存在,太阳行走:列夫﹒托尔斯泰﹑
裴多菲﹑叶塞宁﹑勃朗宁夫人……
命运啊,我被安置在
托马斯﹒曼所描述的“魔山”上,
与莎士比亚笔下小镇里的人物生活在一起,
二十多年间我和伊阿古﹑福斯泰夫之辈打交道。
百万树叶离我有一大截距离,它们的喃喃细语我听不见,
深秋正用黄色﹑红色之手将它们雕刻:
漆黑的主干,银白色的枝桠,
自然的笼子和蜂鸟悬停花畔的片刻时光。
为首的需人与人牵手环抱的古树
伫立在石桥旁:
伸出它们的华盖,多姿多彩,
和举办典礼的标志性建筑相呼应。
各种各样兄弟姊妹般的大树
用枝叶编成伟岸的樊篱
像要把太阳锁住在里面。
偌大的彩色如画的空间
流动着思想﹑分散着触觉,
在蓝色天宇的覆盖下
在这舒适的圆环里,
我宁愿落入那些遍地闪光的网
不思做任何挣扎辗转,
命运的哗变和鬼怪均与我无关;
光明与阴影几乎变成液体
在这里不停地闪耀﹑流动,
人的自设的欲望
不可触及,
空气的藤蔓
将我们做为单独的个体
横加隔离,
甚至连现在也不可触及。
过去完好无损,
过去产生了裂缝:
河﹑松鼠﹑岩石的小径,
太阳用红色的手臂
拍打我的肩,很好,
一切都是虚幻的火焰。
在此之前我已绕行过校区的左面
所见与所想:
那里没有心灵的脚步,
只有思想的阴影,
岁月离散的痕迹,
乍见,空气不是空气
太阳躲在骨制的床后面;
独特的地貌大体上还能辨认,
淡蓝色的山脉在远处互相穿插
——腿肚儿是眼睛能看到它们;
荒滩﹑田野变成了厂房和村庄,
新架起的石桥令人无法阅读,
翩翩白鹭栖息的山岭像蒸发了,
村庄的白墙黛瓦多么耀眼,
——曾经的崎岖山道化为坦途,
那里的里面翻成了外面,
叉开步﹑捏拳还能观望到什么?
呼唤风的树木,
时间从始至终地延续,
兴许赔就是赚;
一切地点在我们之前便已存在
在我们之后仍将存在,
它们是自身又是他物,
没有什么价值可言,
向前看,不值得惋惜,
只是由于我们的心和眼睛
赋予了它们无穷的意义与内涵;
草木的编织像音乐般隆突或低伏:
黑色的草和绿色的树木
或者是绿色的草和黑色的树木,
那织成的鞘翅般绿色的音乐心儿多么熟悉;
——这里的空间
尽情地向拜访它的故人开放:
原初的山野﹑田垄﹑枫林
悄悄地逐一显现,
就像一直被禁闭在这里;
树木一个个张开手掌,撒娇,问好,
我不考虑思想而只考虑形式,
只顾呼吸﹑走路,不顾言谈和现代的变化
在这里我曾是一个顽皮成性的伙伴,
——这里,云翳缓缓地漫天铺展,稻谷金黄,
渗漏出的光线从高而下,光线是水,
时间清澈透明,云和水的草
将我尘俗蒙灰的形象摩擦洗净,
包括此刻我行走而未向前的脚步;
——蓝色的天涯作为导线
转过弯便看见青翠的平顶岗,
近在眼前,
不是梦里的回声,而是实体,
一个岩石化的符号,
上面的植被永远不会再繁衍长高,
太阳压不垮
月亮永久地描画,
其上没有鹰也没有豹
被视作永恒的伴侣;
——这里没有学校,
只有自然,只有自然中的学校
和无院墙的学校朝外拓展化作的自然,
一片海茫茫的绿波,
区域无限地扩大,
青山秀水全都被囊括;
时间曾经在这里凝固不动,
时间如今在我们身上一点一滴地流逝,
曾经并不认为这里是一切
现今却感觉到它代表了一切。
无须知道名字的山村,
躯体在这里也感觉没有名字,
我的眼睛能掠抢多少:
对于冷酷无情的透明
残存一脉柔情的透明?
远山那边——飘忽不定的鹰窠岩的所在
宛若是天神居住的所在,
以我现在由盛转衰的体力
再没有任何富余,
永远不会到达。
清晰的笼子,再见吧,
人永远处在矛盾之中:
美和恐惧在今日已各执一端,
虽然这里的美曾占据过我的灵魂
使我深深地为之迷恋,
——准时﹑豪情﹑信心——
多么奢侈的少不更事的人。
现今勇气﹑时机都去了哪?
不可能有再一次智慧的培育,
山岗已杜绝和我说话,
更高更稳固的山还在后面
再也不见山那边湖泊的波澜;
我感觉到自己面孔的消溶。
我仍旧来自曾经的我。
下午四点钟的座谈会在举行,
声情并茂的演说只是一次次重复。
对于时间的流逝及其重量,
我确定想要说点什么
但什么也说不出:无以言表
语无伦次的嘟囔,
我的头脑中一边是细碎﹑凄切之物
一边正焦灼地想象着——
光明从山峰急速而降,
夕阳的光正在延长,
秋天在将室外的树木燃点,
黄金般的光芒会改变人的面容。
与其坐在屋内说话浪费光阴
不如到一片清晰的空气里
在那些颤动的几何图形的见证下
我们并不是被取消了,
阔别尚不能抹杀我们身上
与它们相似之处的一致,
哪怕仅是片断的现实﹑现实的片断。
一道反光的锋芒划过
我的心田,世界在变轻,
时间像光明一样渗透,
骤然而至的空白
朝我变形的脸和身材涌来,
黑色消瘦的人儿:
曾经载满前程的空气
化作庸碌无为的今朝;
对于绿色的火﹑绿色的血
与绿色的潮我能说些什么,
对于操场上美丽的排斥一切的
强硬的光辉能说些什么,
对于黑色树林中燃烧的
绿色的星星能说些什么……
山峦的峰线在悄悄地坍塌,
白昼越来越像燃烧的蜂蜜,
我看着窗玻璃和窗外的叶片
一门心思地只想走出去,
呈酸性乳汁的故事无处不在,
故事只应该留在书籍里。
终于等到程式结束的一刻:
难道我还在奢望此时
光的菠萝﹑碧绿的冠羽
能帮我加速成形什么?
徒劳地在此地寻觅微笑﹑讽刺﹑未出口的允诺,
一切都来不及了,
苍天的边缘已是旋转的金青石,
空洞的地理不引注意地
在缓缓地转动。
伟大的观念之歌,
可悲的观念之歌,
不可挽回的观念之歌,
云雪中的火焰与武器。
一切皆流,无物常住,
“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
当初人眼睛里的水已流逝,
即使还是这条黄色的河,绿色的河:
河流的眼睛睁着,
瞧着它的人已嗒然无语。
树枝间流淌着火焰
黑影也开始在其中流淌。
一幢幢楼房,
白昼再无幸运的相遇
和奇异的意象的萌发,
时间沉默并且淤塞在此,
太阳尚未老化,
时间已将我们发明,
我们尚够不着粗大的树木的膝部,
大树像已成为未留遗嘱的遗物,
树枝上液体弯曲的火焰
映照我们的眼睛
——毫无目的地使人眼花缭乱。
仍旧活着的树,互相交错的枝条,
沿着堤坝成一路纵队排开,
全都染上珊瑚一样火红的夕辉,
在透明的空间宛若神貌依旧,
岁月在操场上和庭院内旋转,
青春的年华去了哪?
树冠还在显示闪烁磷光的戒指:
却再也不能生产小小的行星
或美丽晶莹之物,
辫形的光线扑打我的脸颊,
花坛之间的大树上
隐约朦胧的广寒宫不见了,
其下,粉红色的仙女不见了,
一座座黄色甜蜜的山峰
也不建在我心中的深渊:
绝美的景物还有什么意义?
我有身躯而没有实体,
同一个事物总是
而又从不是同一个事物,
那使我得以耸立的
一缕精神的气息飘散去了哪?
一切都像无形地被夷为平地,
尽管在此地惆怅地徘徊吧:
割下舌头,捡拾青春的记忆,
在河岸边一切都是意外,
“永无”之琴在头顶上方弹奏,
葱翠﹑朦胧﹑慵懒的景色意欲使我哭泣,
用触觉去观看,用视线去抚摸,
用眼睛将河流的香味儿聆听,
要明白:岁月的轮子一丝一毫
都不可能倒转。
无人能拯救我们,
站在结成连理的大树前,
狼狈不堪的成名成家的野心,
梦想化为记忆的山崖上的云烟。
湛蓝色的远山,湛蓝色
的天空,残破的线形白云,
地面上的黑影在一串串地集结,
岁月肘弯里的温馨之地
浮生之中的半日空闲
使我能和清晰的蓝黑色彩绘似的河流
宁静地相处。
为什么我还在郁郁寡欢:
是有着幼稚举动的少年
与不甘愿沦变作中年人在相互较量?
莫非高高的门道里还留下不忠的尘埃?
一切都源自于太忠诚,
理想﹑意念﹑爱情以及怨恨,
像那些幸存下来的事物一样:
忠实的极至就是否决,
无私﹑谨慎不会带来任何结果。
唉,冷不丁地被他人提起:
曾在冬日里被我焚烧的诗笺,
我和我的幽灵们
冒着雨水严寒去户外
迎着猛烈的冷冽之风,
哆哆嗦嗦地回来时,
那模样落入并刻为他人眼里的一幅肖像。
多少无名的一天(或随便哪一天)
时间掉下来一面面明镜,
世界之母不惜屈尊
做我的卓越的伴侣,
我还是属于迟钝的那一种类型
充满着一种对“思考之无用”的思考,
半闭着眼睛看世界,说梦话,
我的此种溃疡一直延续到今天。
千年的山神,风的桥梁
泡沫般闪光的村镇,
逗留在这个寂静的场院中央
已没有可使之复活的期待和等候,
具有的只是非生命的碎片与微粒。
(什么仍像残酷的鸟儿要啄出你的
眼睛:“愿此处是永恒的浪漫之乡。”)
从隐性到显性,
传奇的化作陌生的,
无法相见的业已相见,
无法相见的就让它们不见,
在尘俗的火焰中来来往往。
个性的冲撞,脾气不合,
趣味不相投,
我和他们都已相互取得谅解或宽宥
甚至片刻便冰释前嫌;
耳畔是一面面空气的手鼓,
眼前是时间阴影的残肢,
我们总是谈论其它的事情。
我不过像一株杂草一样长大,
在树林的胸膛下
反映在幻影中,成为黄昏
赭红色的背景上一星点
怪诞的雀斑。
建筑物
宛似时间的象征,我们凝固的时间。
人变为事物而时间仍然向前
言语行动依然要积极表现的人
在线形时间上也只是个静止的点。
环形时间只在我们头脑中存在:
没有利润,没有增加神圣,
数目可观,而又显得空空洞洞,
譬如眼前这空洞﹑可爱的美景,
在我的意识里倒像成了无人居住的地方。
“事已至此”的不幸,“敢作敢当”的缺乏底气,
多么变化莫测的存在:
用“无常”来解释时间和它的显灵。
终有一天便是这一天!
树木与我皮贴着皮:我身体的
所有身体都进展得太缓慢了。
起裂缝的嘴唇,思维的电流,
“我思故我在”又一次刺激着我,
过去是已消逝掉的现在,
将来是还未到来的现在,
只有一个永远的“现在”:可观,可感,
可行动,没有别的什么时态;
我们谈论“未来”是什么样子,我们都将衰老成啥样子,
谈论“死”和挂在墙上的照片
再过一两个十年是否还能够重逢,
我们在走下坡路,仿佛已若有若无;
我带着一个双重的我重回此地:
像带着一个末路中的我
我也已不再是我。
惟独思绪尚在,我便存在,
我还是我:在这里太阳喂过我,见过太阳
在大树顶上筑巢,
太阳的光线仍旧嗡嗡作响地照射着我,
将黄色和粉红色的迷恋
不停地朝我炮击。
经历了那么多辽阔的废墟和废墟上的
道理,只要活着的意识犹在,
不管时间的时间,我都能一分为二,
我与自己谈心,谈论柏拉图。
我寻找那棵南流河畔的古树,
并没有按照要求讲三个以上的故事,
众多故事只在我的心中跳荡,一个拥有记忆的
躯体自动前来沉入时间的另一侧。
古树像黑色凉亭
一向站立,从不改变姿势,
总是见证,总是沉默不语,
茂密的枝条在暮色中神圣不可触犯。
在它旁边增修了一道平坦的石桥,
高过岸边屋脊的古老的石拱桥
不再显得那么孤独;
彩霞尾随而至
霞光凶猛地映射在浓稠的河水里,
似淡墨渲染的天空,
浓墨粗线条刻画的大地,
偕同而来的人伫立在桥上
映入眼帘的是徽派白墙和远处深蓝色的山岭,
记忆顿时聚集到灵魂的入口
并压抑着与我同来的三人的前额,
穿凿山头的穿山甲们
在这有许多故事像没有故事的地方
抓紧时间拍照留念,
莫管那无形的叹息源自何处。
沿着石拱桥磨损的梯级而下,
我认出并认识那些台阶。
在老街上行走迷失了方向,
凭借不安的记忆判断方位寻找出口,
过去的幽灵全都跑出来
充斥着巷子里的空气,
空气正在挥发着空气。
我们是轻飘飘的过路人,
我们带着呻吟和宝石的尾巴
像要打听什么,可这样做
又有什么目的与意义呢?
具有引力的核心的青石板小径
转眼就已通过,封闭在身后;
我们像双头的鹰一样
被挤压进新街巨大的翅膀里。
记忆里的缫丝厂﹑邮电所
卫生院……都已化作他物,
宽敞的水泥路面在脚下,
一阵昏暗的符咒在我们头上。
“新建筑,新气派!”大片的土地
被征占,一些美好的﹑白热的时辰
所发生之地永失踪迹,
一声沉重的﹑残忍的叹息,向着天地间
它将我自己腾空,荡平我的存在。
到处华灯初上,夜幕降临……
有展台吗?有。
一个纹着符号的身躯屹立其上
像站在昨日与今日之间,
灯光在大厅里演说,贴画在歌唱。
几大桌酒席已经为我们摆上,
谁愿意回味过去就请留下,
人会在开始的地方分成两个人。
我的面孔脱离了我的面孔
——徒劳地浏览自己的生平有何用。
窃窃私语,笑声,交谈,
干杯,滚烫而又模糊。
唯我论,迎接现在的我们。
爱情与梦想:什么也别想,
我享乐主义的同类。啊,“意象完结了,结构瓦解了,
啤酒的泡沫,何所谓强有力的哲学?!”
走出灯光——旅馆
有人挽留不住地去了便不再回来
像离开曾经充满白炽灯光的教室——
像历史上屈原﹑窦子明﹑李白
时间或长或短漫游过此地。头晕眼花,
鸦雀无声的寂静,
黑夜的主人并不打算让我休息,
被人邀约三五成群地去逛夜市,
深入到寂静之中
没有实体的概念,
只有飘浮的时间。
在小酒馆与同伴一起重开酒宴
不要等候,不会再有人来;
在开始的开始的地方
酗酒,体验再一次在寂寞的半夜街道上横行;
在星体与躯体相连接的地方
徘徊不定地哭泣;
为了知与梦的年代一去不返,
为了明日的告别,
沉默不语或放肆地打喷嚏
响亮地笑:反正都一样。
“所幸的是我们当中还没有人
在半道上夭折,
一个个都还健在”;
我还在喝着起泡沫的啤酒,如同
饮着沟渠里的血,看见
光秃的山峰﹑磨平的骨骼和滚动的石头
(而后,有人粗鲁地踢啤酒箱,别喝了,
“别管我们的相貌,是否过得太老,
或是评论有的人过得也不好”)。
我在自己的梦呓和故作的狂欢上:
“可惜,已不可能再有知音陪伴,
你永远孤独一人;”
我的声音结束了
必须要自给才能生存,
我的耳朵我的预见我的操劳
刻上自己的笑容与呻吟,
目光被破坏了又能怎样,
还有记忆的篮子;
叔本华﹑尼采,不是兄弟的兄弟,
他们教导我说:“作为表象与意志的世界”,
然而那只是一种黑色的观念,
我只想着那些成为我的身上之物;
他们同亚里士多德﹑黑格尔,柏格森和怀特海
一样,挥发坚实的理论的白色;
崇高而又严肃的夜晚,寂静的喷流,
人本主义总是为时太晚;
不是“纯一的时间”,
我愿意谈一谈有关真正的时间绵延的学术。
还有马斯洛的本我﹑自我和超我:我懂得
乌七八糟的不该懂得的一大堆东西,
“我知道,我一无所知”,
写作又算是一只什么样的鸟。
音乐的松树牢牢地站在黑夜之上,
我面朝着天,听着黑夜唱时间模糊的歌,
确切地说那是一方时空的颤音,
时间裂成两半,请时间不要出现:
我们是无名的瓦砾,不是吗?
转过一条街道,
与新街道对直的空隙处崭露夜空的一角:
璀璨的星光霍地呈现,
星星个个大放光明,拥挤又喧闹
像要急切﹑荒诞地朝我的脸
靠拢。其他人对此竟浑然不觉
除我外像没人看见。最后的显示,
梦想并不值得。
黎明已经降临
黎明没有任何味道
——也没有一点儿气息。
它还是吸引着我早早地向郊外而去
准备凭吊或者去抓最后一条声音的尾巴。
一弯残月悬空,洁白而又寒冷:
像锋利的刀刃一样散发光芒,
世界在晦暗与变白的不稳定之间变得虚无飘渺;
肉体微弱的火焰,怀着什么目的
进行怎样一场最后的对话。
三十年只是一个瞬间……
语言完结了,说与不说都一样:
致命的拥抱,创伤的源泉,
山水的国度变成了“荒漠”
一切形体的奔波和它的悲剧
人间有“死神”,也会有死人,
如此大放悲声有何用?在时间空虚的秘密面前
高声宣扬来此地的秘密感受有何用?
不会有谁聆听,
它们抖动在
一个玻璃般的空气的桶里。
惊呆的肢体,
被堵住的嘴巴:
一切都在用栏杆把我阻挡使我成为陌生人。
云彩已经散开:万物准备它们在白天的存在。
在一秒钟内庆祝“光线”的降临,四周静悄悄,
我的眼睛成为两个神奇的了望塔,
孤独一人的走动,
花草开始醒来。
一个倾身于往昔的人,想要再一次领略
此刻躲在某处窠臼里的那些白热的鹰。
水﹑火﹑风﹑土这四大元素
构成自然世界,人也是由这四种元素
混糅而成。不外乎此。一个分隔与撕裂的火花
跳在我说“话”的双唇上:
嘴巴什么话也没有说。
从早晨六点开始
来到校区的右侧面,
又发现一座后来才架设的石桥。
我站在开设于三个惊叹号之间的桥面上,
看着墨绿的翡翠般的河水
淡黄色的浮萍:旧时光再也回不去了。
在绿色和黄色之中发笑吧:
拜伦﹑小仲马﹑川端康成;
一切都只是天真的游戏,
游戏演化成为生命的历史,
进而将一个躯体化变成为草。
坚持,自卫,坚持,
弄成今天这样子可不是闹着玩,
同雪与盐的对话正式开始,
洁白在等候着被矗立起来,
东方的翅膀军团穿过天空,
向前,向前,只要我尚未使自己完结。
耳朵里有不为人知的一个蜂巢,
从眼中生出一只鸟儿,
与自己的灵魂搏斗,
在时间和形式之下:
跌倒,爬站起,再向前。
看似盲目而且没有止境。
与自身的抗争不足以向外人道;
失去天空的目光,失去大地的目光
也不方便向旁人阐述;
在磨难中,每个事物都必须要挺立起来,
每个事物都在抗争并排斥着其它事物,
因此,不要想着有解脱的时间,
全是自己为目标而牺牲的时间。(持久的思索,
无限的敬仰,人头顶上的星空只被康德发现)
一个小的心愿外面是更大的心愿,
时间的态度含糊,寂静和孤独
使自己的原野不断地蔓延,
面对着这一种无垠﹑昏睡着的眼睛的风景,
在人居住的世界啊:
孤独的追求是因为何种崇高的事物——
难道只是像从少年维特过渡到年老体衰的歌德:
为发现年轻时代在岩壁上镌刻的痕迹
而失声痛哭?
幸福或痛苦都会变成历史。
岁月的隧道﹑历史的走廊里没有别的,
永远是战斗着活的“牺牲品”,
朝着死亡这唯一的出口:
或许人只应该站着死去。
历史由人来创造,由人来书写。
我在途中,越来越不中用,
现在回来了,奔向我的诞生,
迎接我的只有陌生渊薮中的碎片:
已经开始的是我“这个人”回不去的更是我“这个人”。
现在只有我“这个人”而没有曾经的那个我。
我非我,花非花,
地点虽然还是那个地点,
它早已将我“这个人”废除,在名称上
更是与我保持着很大的距离。
过桥:
顺山势蜿蜒的土路已变成水泥路。
邻近的山坡被挖掘掉一截
像野兽的后腿上被撕走一大块肉。
这天然的作品不受任何保护,
它努力依靠自己保护自己
大自然向来如此;
一户户人家的
漂亮的楼房,汽车,小院,
生活条件明显地改善,
这不是我想要看的——是别的,
沿着弯曲的大路梦寐以求的东西
已经临近——它兴许也正前来
将我迎候。
但是,这一片山岭,
草木不再向我伸出温柔的手臂,
我也不再令它们的心——感到高兴;
荒芜,孤独,寂寞难耐,
哪里还存在“诗意的栖居”,
正如荷尔德林的悲吟:丽人啊,日光下
到处看不到你……。
多么久远的事,在风的呼吸当中
在时间之神的口袋里:
幸福的面庞已远去,
生命的妙音已绝响,那边:
美人所停留过的地方
仿佛还是昨日的情景。
时间流逝而又没有流逝;
眨眼的伤口,眼前空空荡荡,
时间可以确定已然流逝
这里只是纯粹的空间。
灵魂已经空虚,大地的面目犹在,
但内容已经被抽除。
我行走却又驻足,时间有限,
不得不继续行走。
除了尖山顶上的草木,像没有什么能留下来;
向着礼貌山的方向致敬,
线形时间只有这一种状态。
线形时间:
过去了便不再来,过去的
既存在又不存在:存在是由于经验﹑
记忆的引领,不存在是因为有现在。
地理﹑空间就要简单许多:
人不来,就不会有显示和呈现。
而活着的事物都朝着分散的方向。
分散和变迁是常态,
没有什么是永恒。
此刻我便在自身中溶解,
看不到过去的门﹑微笑,
触不到诗的黑色与白色,
可是过去还在连续进展,
过去总是紧紧咬住未来,逐渐膨胀
直至无限;
我倒愿意相信
是由火转化成的万物
万物不断地变成火:
时刻的花冠
讲着火焰般的话语
转瞬即逝;
人的名字和形象建筑在空气上,
生命的有机体在冒烟,在看不见地绵延,
形体在时光中变样
形体最终会消亡。
我现在已无资格
要求粗犷的梦,
对那些流浪的小路
或是对称又反常的山谷
我已彻底丧失勇气去征服;
别了,连绵百里的青山:
巍巍耸起的屏障,
直插云霄的山岭,
高岗之上我曾是唯一的恋人。
没有钟点的时间
我却感觉到它的有限。
没有形体的寂静
起来又落下,落下又起来,
我对它偶尔巨大的铲动已不感兴趣,
隔着一大片枯黄色的田野
朝着河流细细的上游眺望:
那儿草木茂盛
高堤仍在,可能已没有草滩,
在那里我曾是个真正逍遥的人。
做为一个观察者也被所观察之物观察,
树叶染红的杂木要从斜坡上走下来,
身侧有披垂的巴茅﹑鲜红的小野果,
再往山坡高处生长有竹林。
不远处山岭脚下有杉木林。
依偎着近旁山角的是弧形的稻田,
从我走着的路上往下迈几步
便可伸手触及发亮的池塘,
所有景物的“排列组合”都显得无比亲切:
它们承载着有心灵活动的故事,
让听觉享受到秘密的音节,
让眼睛看到时间的背面——
一派令人陡生凄凉之感的景象,
我曾经所无比期望的幸福
统统化作云烟,在空气中自行消散,
甚至不能算作是一个半完成的隐喻;
我听到了自己无用的心声
在现实中永远没有“成全”,
螺旋体的思绪,诗歌,
我在我曾在的环境里
正作转向,走在光滑的土路上:
两条雪白的车辙印痕慢慢地合二为一;
那么多当初认为的有用之物
竟是实实在在的无用之物,
背负着“错误的东西”注入的一切
回想自己的所作所为没有一天是“对”的:
而这“错误的东西”与我眼前的环境
紧密地相联,
只有在这里它们才有意义,
才又有了符号和磁性的振动,
让人不惜为之赴汤蹈火。
到来即预示着离开,
相聚即意味着更长的分别,
时候已不早,我得原路返回,
时间像水晶的球体从我怀里滚落,
我听从自己的脚步,我既充实又空洞,
我会怀念这地方,它可不一定想我。
我该向泛起锈色的植被说声再见。
2018.11.20——11.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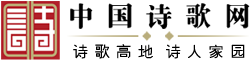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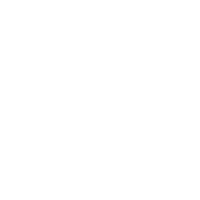

 (2次)
(2次)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34246号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34246号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