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崖丽娟诗访谈”:敬文东|新诗必须拥有它的自我意识
敬文东答诗人崖丽娟十问
崖丽娟:敬教授,很高兴有机会访谈您,在您的论著《新诗学案》中有这样一段话:“不是说一首诗好懂就是无难度的,也不是说一首诗晦涩就是有难度的。有些看上去很简单、很易懂的诗其实难度很大,因为它处理的问题很多,只是这些问题被才华甚高的诗人悄无声息地消化掉了;有些看起来晦涩的诗,其实简单之极,徒具修辞效应而已,某个人一旦掌握了这套貌似难以掌握的招式,就可随意套用,就可以写出同等程度的晦涩、难懂之诗”。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诗是一种手艺,诗人,必须具有匠人的耐心、气度和聚精会神才能打造出真正的艺术品。
敬文东:新诗之所以能够出现,有理由诞生,原本就是为了应对复杂、难缠的现代经验。一部糊里糊涂的文学史早已表明:这种复杂、难缠的现代经验,非古诗所能表达,旧瓶装新酒乃是一厢情愿之事。古诗的拥护者对此可能持有异议,但这终归是事实。时至今日,该事实已经毋须论证。这样说很可能意味着:新诗至少在难度上,非古诗可堪比拟。比如,《诗经》《离骚》等等,因为古今之变,最多只有训诂学或名物学上的难度;在对诗意的理解上,不存在任何困难。但这一点,并不影响古典汉语诗歌的伟大和辉煌,因为它原本就该是那个样子;古诗几乎是在完美的层面上,完成了或满足了古人的表达欲,记录了古人在万事万物面前精微的灵魂反应。任何艺术都必须要有技术方面的严格训练。古诗新诗在这一点上,不该有性质上的区别,只是各自的技术指标大不相同而已。废名先生早就说过,古诗是散文的内容,但具有诗的形式;诗的形式加散文的内容,构成了我们伟大的古诗。几年前故去的流沙河先生认为,赋、比、兴是古诗的修辞基础,一首诗也许可以没有比和兴,但绝对不能没有赋。赋应该更靠近散文这一端。陆机不是早就讲到过吗,“赋体物而浏亮”嘛。废名还说,新诗是散文的形式,但必须得是诗的内容;诗的内容加散文的形式,构成了我们经历太少的新诗。所谓诗的内容,就是这内容不可能用散文转述,不能被散文置换。把古诗翻译成现代散文,没有任何问题,余冠英选译《诗经》、郭沫若译《离骚》,堪称经典例证。也许只有很少的例外,比如将《锦瑟》译成现代散文,至少在我看来有一些难度,但更有不忍心的成分掺杂其间。所谓散文的形式,反倒意味着一个极难完成的任务:每写一首新诗,就得发明一种新的形式;形式永远处于开放而被发明的状态,只要新诗还在继续着它的生命。当然,懒惰的诗人除外。一百年来,一直有人想为新诗寻找某种、某些格式化的形式,以确保对他们而言,新诗的长相看上去确实像是他们心目中期待的那样。唉,这些痴情的人们,到底没能弄清楚新诗的门道。
总而言之一句话,面对晦涩、不透明的现代经验,新诗必须表达难以被表达的情感(我将这种状况曾经表述为“必达难达之情”)。对于某些诗人来说,也许选择很简单的修辞、发声方式、调性和口吻,就能将“必达难达之情”,也就是新诗最重要的技术指标之一,给很好地克服掉。我在这里愿意挂一漏万,举三个经典例证:卞之琳的《断章》、昌耀的《紫金冠》和宋炜的《登高》(之二)。当然,也可以用非常复杂的修辞方式和言说姿势,解决必达难达之情。在这方面做得非常极端的,当数英年早逝的张枣。作为张枣最早和最有力的批评者,钟鸣甚至认为,张枣使用的每一个关键词,都是一次性的;张枣不允许某个重要的词出现第二次时,其语义竟然完全等同于它第一次出现时。发明新的诗歌形式对于张枣来说,就更是苦心孤诣之事,耗费了他无算的心血。这也许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张枣留下来的作品少之又少。但修辞决不可滥用(或烂用)。无论看起来多么具有难度的修辞,一旦成为某个诗人使用起来极为趁手的东西,就一定会走向词生词或词语装置物的境地。新诗史上,这方面的例证实在太多了,以至于到了毋须例举的程度。
崖丽娟:经您分析和梳理,我理解新诗一个重要任务或作用就是必须要准确地表达难以被表达的情感。您在《新诗学案》中对吉狄马加、西川、欧阳江河、宋炜、西渡、杨政、柏桦、冯晏等优秀诗人的个案分析确实可以找到这种共性的东西,此外,您觉得好诗还有那几条标准呢?
敬文东:很难说有啥共同认可的标准。但有一条,大体上还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对语言和形式的细心经营。恩斯特·卡西尔认为,艺术给人带来的,不过是对形式的享受而已矣。这等享受,当然必须依赖诗人和其他艺术家们的殚精竭虑。新诗是现代汉语的产物,但同时也是现代汉语的受益者。也就是说,一个好的诗人,必定会对他仰赖的现代汉语有所贡献。您刚才提到的那些诗人,多多少少对现代汉语都有所增益,但他们首先是现代汉语的受造物和受益者。在1840年以后的中国,最先具有现代性的,当然是语言;语言的现代性的产物,当然非现代汉语莫属。这在眼下,已经是不需要证明和论证的常识。在这里,我特别想强调的是:我们今天遭遇到的一切现实,无论好的,还是坏的,无论不好不坏的,还是不那么太好也不那么太坏的,一概导源于表面上不露声色的现代汉语。被运用的现代汉语自身是从不说的,也是从不说现代汉语自身的。但现代汉语目睹了它自身被运用时,产生的一切后果。这个话题太大,但主要是和我们眼下这个对话没有直接关系,要不,暂时按下不表吧?经由现代汉语,中国人才得以渐次进入全球化时代和地球村时代(马歇尔·麦克卢汉语);经由现代汉语,中国诗人也才能享用“语言转向”带来的全部后果——这个问题,就和我们此刻的对话有关了。
仅就积极的一面来说,作为被现代性包围、浸润的现代人,新诗的写作者必须承认:作为文体的新诗必须拥有它的自我意识。这就是法兰西的天才诗人兰波所谓的“话在说我”,而不是“我”在“说”“话”。不言而喻,“话在说我”意味着:“话”对于“我”而言,具有明显的优先性。但明确认识到“话在说我”这个令人诧异的语言现象,即使是在西方,也不过是20世纪的产物——它可以被认作语言转向的产品之一。因此,新诗写作者和古代的作诗者大不一样,古诗的编织者可以主宰古诗这种文体;古诗不过是“言”说古代诗人之“志”的某个器官。古诗作为一种文体,具有强烈的工具论色彩,没有任何自我意识可言。新诗写作者必须和作为文体的新诗商量、博弈、谈判,以便生产出一个双方认可的抒情主人公。抒情主人公是诗人和作为文体的新诗,依照平行四边形法则虚构出来的人物。但这个被虚构的人物非同小可:抒情主人公说出的话,被诗人以书记员的身份记录下来,这就是最后凝结成型的新诗作品,当然,称诗篇也许更恰当。新诗作为一种具有现代性的文体,只为现代中国人所专有;一切优秀的诗人或诗篇,都得建基于将新诗理解为一种现代性的文体。
崖丽娟:有人认为在整个现代性的实践上中国新诗已经走得很远很前沿了;同时也有人不断诟病新诗晦涩“读不懂”。对于“当代诗歌阅读何以成为问题”许多批评家纷纷寻找解决良策并给出不同的答案,但似乎仍“一厢情愿”。您在解决读者“懂与不懂”方面有何妙招?
敬文东:我想,大概没有人会为自己弄不懂广义相对论或者麦克斯韦尔方程式,就去抱怨广义相对论或者麦克斯韦尔方程式吧。很奇怪的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因为读不懂现代诗而抱怨现代诗,却不抱怨他自己呢?我很好奇:究竟是谁给了他这样的特权,以至于可以耍这样的小性子?记得很多年前,有一家著名的海外汉学刊物的主编找到我,命我约请张枣吃饭(我早已忘记他找张枣吃饭的目的了)。假如你想,张枣会拒绝一个陌生人的饭局,那你肯定错了。张枣那样的超级吃货,怎么可能拒绝这等好事?再陌生的人也无所谓,再危险的酒局也要参加。酒过三巡,这位主编说,他确实对现代诗感到发怵。现在想来,张枣差不多是以很少见的严肃态度告诉他:读懂现代诗需要专门的训练。张枣的潜台词也许是:这就有如你想懂得广义相对论,需要专门的训练一样,只是方式不同而已。我的看法很简单:对于那些因毫无训练而读不懂现代诗的人,应该采取不予理睬的态度。有些人连自己的老婆甚至连他自己都搞不懂呢,但这归根到底关我们什么事呢。另一方面的实情,却又很残酷:中国的大学的文学院里,懂文学的人原本就很少,教文学不一定懂文学,这就是当今的行情;要想让这些人以其昏昏启人昭昭,岂不是咄咄怪事?奥登回答过某个好事者的提问:写诗的前提到底是什么呢?思想?学问?才情?奥登说,no,no,是对语言的超级敏感。一个人一生中,如果没有一次对某些词语、某些句式有过如遭电击般的感觉,就最好不要接触包括诗在内的任何语言艺术。但这并不意味着写诗、读诗不可以训练。在所有形式的训练中,自我训练最重要;在所有形式的自我训练中,多读、多琢磨、多比较尤为重要——对一个好学者来说,比较才见分晓。如此这般,假以时日,一定会对现代诗有所领会(至于领会多深,那是另一个问题,此处不表)。中国有句老话,还很有可能是朱熹说的(我懒得去查):书读百遍,其义自见。除此之外,不存在更好的办法。每一个行当都需要天赋。也许某些人对此会怀有疑问:你这不是把话给说满了吗?难道种地也需要天赋?我的回答很简单:假如你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人,倒不妨去试试?曾经有一位著名的盗贼说过,好的读书人过目不忘,好的盗贼对他到过的地方也过目不忘。此人讲的就是天赋。拉杂说了这么多,我特别想说的其实是:你有这个天赋,就自然会懂现代诗,没有呢,那就永远不会懂。这就像喜剧演员陈佩斯说:良心这个东西,你有就有了,没有就永远没有。这真是得道之言!但在此我最想说的是:懂现代诗没什么了不起,不懂现代诗根本就无所谓。以我看,你只要懂得其他技艺用以防身和谋生,就足够了。
崖丽娟:我很赞同您的观点,可是依然听到质疑新诗的声音。在新诗遭遇诸多质疑的当下,亟需真正的批评,更需要真正理解批评。作为诗歌批评家、诗人,您如何看待诗歌创作与诗歌批评的关系。
敬文东:创作和批评是两个行当,但都应该是创造。写诗是创造一个全新的世界,批评是面对作品建造的全新世界构建批评的空间。它们的共同主题或对象,是人作为个体和种族在宇宙中的命运。不触及命运的任何文字都不值一提,至少不那么重要。我曾在不同的场合,多次强调过同一个观点:文学批评固然需要解读各种优秀的文学文本,但为的是建构批评家自己的理论体系;而文学批评的终极旨归,乃是思考人作为个体在时间和空间中的地位,以及人类作为种群在宇宙中的命运。打一开始,我理解的文学批评就具有神学或宗教的特性;不思考人类命运的文学批评是软弱的、无效的,也是没有骨头的。它注定缺乏远见,枯燥、乏味,没有激情,更没有起码的担当。我当然不会错误地认为文学批评家居然可以是牧师,也不会浅薄地将批评家认作神父。事实上,他们只是一群喜欢思索、乐于思索的人而已。他们更愿意从形而上的角度关心人、关注人和观察人,但他们首先是观察人如何被作家和诗人所表达,人的命运在何种程度上具有何种宽广的可能性。在此基础上,批评家乐于在战战兢兢中,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做出极为谨慎的预言。他们愿意报告人类未来的消息。他们愿意为此负责,并成为风向标。我马上想说的是:难道这样的任务不同样属于诗歌写作吗?就这个意义而言,我当然可以说:批评家也可以是诗人,另一种创作者。诗人亲自上阵进行批评工作,其实是很正常的事情,说不上是对批评的不满,就像批评家写诗,说不上是对诗歌或诗人的不满。历史上,同时将优秀诗人和优秀批评家兼于一身的人不少,同时将优秀批评家和优秀诗人兼于一身的人却不那么多。不过,这并不重要,只要他们对命运有很好的研究、考察和思索,就算履行了他们的职责。
崖丽娟: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现代诗是从外国诗歌演变和引进的,甚至有人说不读外国诗,很难写出具有现代性的诗歌。新诗之所以被诟病“读不懂”是不是还与它的诞生有关?诗人如何处理“翻译体”与母语写作的关系,其实对应的正是新诗如何面对西方现代诗和中国古典诗歌两大传统。
敬文东:翻译体自然有它的问题,但我们必须承认,现代汉语的来源之一,就是以翻译体为桥梁。我们不能过河拆桥或忘恩负义。早在1940年代,郭绍虞先生在《新诗的前途》一文中,就这样说起过:“新诗中原不妨使之欧化,但必须先有运用母舌的能力,必须对于国情先有相当的认识。欧化而不破坏母舌的流利,欧化而不使读者感觉到是否中国的背景,那也是成功。”郭氏的断言相当精辟,但首先是它秉持和具有的客观性。《马氏文通》是现代汉语的第一部语法著作,它主要是仿照英文的语法来构建汉语的语法。不管现在的学者对此有怎样的批判和反思,事实上,它在很大的程度上型塑了现代汉语的全部腰身。我把这个过程理解为:味觉化的汉语演变为视觉化的汉语。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神农尝百草的故事,这个故事意味着:中国古人是以尝的方式认识世界,古人使用的汉语以舌头(亦即味觉)为中心。英语或拉丁语系建立在视觉的基础上,现代汉语因此更主要是视觉化的,是分析性的。它远观万物,不再与事物零距离相接触。古诗和新诗因此展开的是两个非常不同的故事。视觉化的汉语为新诗条“分”缕“析”复杂的现代经验,提供了很好的基础。如果说,古诗是直观性地有所看,并且把看到的东西写下来就可以了;那么,新诗不仅要有所看,还要看见正在发生的这个有所看(可以简称为看-看)。现代汉语为看-看提供了基础。古诗的精确是整体氛围上的精确,所谓身临其境或情景交融;新诗的精确是分析性层面上的精确:看监视、监管有所看带来的,是每一个细节上精确。细节是分析的产物。
这个问题很重要,不妨稍微扯得远一点。《红楼梦》第三回如此描写林黛玉:“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闲静似娇花照水,行动如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这种描写是氛围性和情景交融性的,是意会而非实写,是从感觉的角度进行的描写,曹雪芹使用的汉语很擅长、也很乐于实施这样的言语行为。老舍对此有诚恳的批评:“这段形容犯了两个毛病:第一是用诗语破坏了描写的能力;念起来确有些诗意,但是到底有肯定的描写没有?在诗中,象‘泪光点点’,与‘闲静似娇花照水’一路的句子是有效力的,因为诗中可以抽出一时间的印象为长时间的形容:有的时候她泪光点点,便可以用之来表现她一生的状态。在小说中,这种办法似欠妥当,因为我们要真实的表现,便非从一个人的各方面与各种情态下表现不可。她没有不泪光点点的时候么?她没有闹气而不闲静的时候么?第二,这一段全是修辞,未能由现成的言语中找出恰能形容黛玉的字来。一个字只有一个形容词,我们应再给补充上:找不到这个形容词便不用也好。假若不适当的形容词应当省去,比喻就更不用说了。没有比一个精到的比喻更能给予深刻的印象的,也没有比一个可有可无的比喻更累赘的。我们不要去费力而不讨好。”老舍的批评当然有道理,但他是以现代汉语的分析性,去检讨古人使用的汉语所擅长的抒情性,让人不免心生一种搭错车的感觉。
翻译过来的各国——尤其是欧美——的诗歌作品,当然是新诗写作的重要参照,是诗人和批评家的营养之一。新诗固然用现代汉语,但现代汉语毕竟还是汉语,这就保证了新诗并不会完全自绝于古诗。传统不是遗物,而是遗产。对于中国人来说,汉语和汉字无疑就是最为重要的遗产。至于如何将古诗的精神化入新诗,是每一个诗人的任务。就我的观察而言,也许钟鸣、张枣、宋炜、西渡、蒋浩等人取得的成绩,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崖丽娟:网络时代既给诗歌发展带来机遇也带来困扰,不计其数的微博、微信、各类公众号平台扮演着公民诗歌训练场角色,这对诗歌的健康发展是否有推动作用?好诗会在看似一派繁荣的网络诗歌中诞生吗?
敬文东:诗是一项古老的艺术,几千年来,没有听说过因为出现了某种新媒介,就让诗更繁荣,或者就让诗的整体质量得到大幅度的提升。网络新媒介肯定会给诗带来前所未有的热闹,这些热闹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它就在我们眼前。至于网络新媒介是否会给诗带来更多的读者或听众,尤其是高质量的读者或听众,我有理由持怀疑的态度。诗应该和安静联系在一起,诗也许永远都是献给无限的少数人的东西。它的繁荣与否,和媒介没有多少像样的关系,顶多和诗的传播有些关联。
崖丽娟:您长期在高校进行诗歌教学和研究,本人也写作诗歌、小说、随笔,有丰富在场写作经验,不仅自己著述颇丰,而且桃李满天下。您的学生曹梦琰写的《我的导师敬文东先生》一文,读来可谓妙趣横生。您的学生中颜炼军、张光昕、王辰龙、杨碧薇等都很优秀,正在跟您读书的张媛媛、王婕妤、夏至等也已崭露头角。您是如何做到“教学相长”,在课堂上如何教授写作与欣赏的,有什么教学体会和我们分享?
敬文东:如果他们真的很优秀,那主要是他们自己聪明、努力,最多是我和他们相互学习、彼此勉励的结果。我推崇这样的师生关系:我和他们经常一起喝酒(我喜欢喝酒哦),在酒桌上其乐融融时,不谈其他的八卦一类东西,主要谈读书、写作;互相推荐书籍,或者在酒桌上直接评价自己正在读的书。凡是我们有新作,必定相互交流。这等情形,有一种古人所说的“从某某游”的读书氛围,多多少少有点私塾性质吧。这是我推崇的方式,既能收获学识,也能收获友谊。
崖丽娟:许多人认为诗歌是灵感的产物,写诗究竟是以理论指导创作还是创作跟着感觉(灵感)走就可以了,写好诗有窍门可以教、可以学吗?
敬文东:虽然我的职业是教师,但这只是我的谋生手段。实际上,我对好为人师确实兴趣不大。这个问题,我就不回答了吧。
崖丽娟:您好像自谦说过这样的话:“当发现自己再怎么努力也成为不了好诗人时,最终放弃做诗人的梦想”。其实您的诗写得很好呀,2022年3月出版了诗集《多次看见》就反响不俗,当然,与写诗相比,诗歌批评确实占用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据了解,您对鲁迅、历史、小说和思想史也都有研究,您还放弃了做物理学家的梦,是这样吗?
敬文东:实在抱歉,我个人的事情没必要在此叙说。如您所知,我是一个很普通的学徒。我发誓,我愿意成为一个终身的学徒。实际上,这个学徒不过是喜欢读读写写而已。
崖丽娟:对于优秀的诗歌批评家来说写诗是否是必要的呢?您的诗歌写作曾停笔多年,重新拾笔创作的契机是什么?从诗集《多次看见》可以发现一些您较为偏爱的意象,比如“山楂”“房间”“酒”(对,您上面说过喜欢喝酒),这些意象背后是否有什么特别的含义或故事?比起批评文字坚硬如铁,铿锵有力,您觉得自己的诗歌是否展现出不为人知更柔情的一面呢?
敬文东:您锲而不舍,不想放过我,是吧?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我们这些1980年代中后期上大学的人,没有喜欢过文学的可能没几个。我一方面是从俗,确实阅读了古今中外不少文学作品;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从初中一年级开始,就喜欢胡绉一些所谓的诗句。想当诗人,在1980年代是再普通不过的事情,实在没什么稀奇。批评家是否写诗,原本不是问题。写诗和批评确实是两个很不相同的行当,但如果某个批评家偶尔写诗,也不是什么坏事情,更不是什么大事情。比如,我认为作为批评家的陈超、耿占春、张桃洲等人写下的诗,完全可以和职业诗人相媲美。但职业诗人写下的诗,都一定是顶呱呱的诗吗?这是很值得怀疑的事情。我自忖,我从2019年开始重新写诗也没什么契机,不过是觉得有了一点诗兴而已,何况从那时到现在,也不过写了17首,而且质量参差不齐。至于您说的“山楂”“房间”“酒”这些意象的背后,也没什么故事。我反复回忆之后还是觉得,我应该是个没啥故事可言的人。和批评文字的面相多样很相似,诗歌也该有无数种面相;您所说的“不为人知更柔情的一面”,也只能是无数种面相中的一种吧?也许还不是多么具有代表性的那一种呢。您尽可以认为,以这等语气和态度回答您的提问,确实有些生硬。但我的回答,确实愿意距离诚恳、诚实以及事情的真相更近一些。如此而已。
崖丽娟:感谢您诚挚坦率的回答。
敬文东:应该感谢您的提问。
(2022年7月9日,北京魏公村。)
附:敬文东近作选
最小的事情
我一直做着人世间最小的事情,毋须
背叛任何人以取悦于我之所做;我也未曾
被任何人出卖,因为我一直做着
人世间最小的事情。如今
我已到了极目之处尽皆回忆的
年纪,即使借我豪情和悲怆
也无法让我拒绝微风、落叶和
飘零。我少不更事时礼赞过的
山楂,和我一直做着的事情一样
渺小。但它毕竟有过红彤彤的
时刻,不似我数十年如一日地脸蛋黝黑
活像我做出来的那些最小的事情。
我来了,我看见,我不说出。
(2020年10月21日)
拯救者
我曾把最好的年华,委身和委弃于
愤世嫉俗。在阴暗的日子里,让我免于
崩溃的鸡汤是:人生无意义,但某些事情
对没有意义的人生有意义。比如:
读书、写诗、醇酒,没有妇人。
但最终拯救我的是汉语,是汉语的
仁慈、宽厚和悠久,但更是汉语宠幸的诚
王船山说,诚即实有。多亏了实有。
我正在去往超市的路上
心里头满是氤氲之气
看,沿途的店面多么健康
活泼、率性和乐观;梦境环绕在
它们的头上,对称于我日渐苍老的
心室和心房。我是说,我要去超市
购买这个季节刚下山的瓜果和蔬菜。
(2019年10月17日)
银杏之诗
poems are made by fools like me,
but only god can make a tree.
诗是我辈愚人所吟,
树只有上帝才能赋。
(菊叶斯·基尔默:《树》)
秋已深,天渐凉
每年如此,今年不得不如此。
银杏叶如期变黄。叶们脱离枝丫
在空中画着弧线,像叹息。
轻轻飘落地面时
银杏叶有难以被察觉的颤抖和
细微的痉挛,那当然是叹息的
尾音,倔强、不舍,却又甘于放弃。
从远处看,银杏的枝头
挂满了叹息;
细查五千年华夏史,银杏叶
乐天知命,倾向于消逝。
当你突然看到一颗秋天的
银杏树,你一定要说服自己
你是个有福之人。
(2020年10月21日)
一年将尽
洗去砧板上最后一点污渍,又是
一年将尽之时。那污渍
是给上学晚归的女儿做菜时
留下的瑕疵。
它不是污点,它不过是
生活的叹息,倾向于转瞬即逝
我在心中暗自唱了个肥喏,郑重地
为它送行。
它刚走,女儿的短信即来:
“我已到紫竹桥,你可以开始炒菜。”
无用的书生旋即分蘖为有用的厨师,
油盐酱醋、姜蒜葱花
爆炒、生煎和提色。
盛盘完毕,钥匙入孔的声音
响起,女儿像一阵轻风
吹散了她脸上冻僵的红晕。
一年将尽之时,餐座上
有热气腾腾的回锅肉,还有
西红柿鸡蛋汤,像是唱给新年的
肥喏。
(2019年12月31日)
土门村,汉语
这是我曾经见过的落日中
最像落日的落日:从容、慈祥,温润如玉
正走向每一个生命日的终点,顺应于更高的意志
赋予它的命运。我看见土门村的落日
正在翻向山脊的另一面。众鸟起舞,给太阳的陨落
以庆典;也给它遵从汉语的教诲自动臣服于命运
以褒扬。当然,此刻的落日与其他落日一样,迥异于
旭日。初升的太阳倔强、执拗,像不服输的
孩子,视抗命为乐事;更为自己正在抗命兴奋得
面红耳赤。落日被汉语喂养,被汉语
润滑、舔舐;旭日跃马仗剑,更像雅典的勇士
远走天涯,个个都是逆命而上的普罗米修斯
在北京的街头看到落日的此刻,我五十岁;和我在土门村
看到的那轮落日相隔四十年。土门村的落日没能
让我联想到汉语、希腊、罗马和普罗米修斯
现在,我念及它们,仅仅是因为神情恍惚?
(2019年10月12日)
十三不靠
是不是只有实现了的,才更现实?
而凡是消逝了的,肯定永远消失了。
那些纸做的花,是否有资格嘲笑
没有资格做成花的纸?
把你不开心的事说出来让大家伙开心一下
真的能升华为一件舍身饲虎的事吗?
老人和小吃之间构成的修正比
确实很迷人;婚礼主持人用葬礼口吻
主持的婚礼,则极富预见性。
蒲公英射向紫云英的那束目光折射为
三束反光;白中的黑和黑中的白
喝了鸡血酒后,就结为了兄弟。
秃驴和黔之驴在相互作揖;
彼此和彼岸终得以彼此为岸。
强奸和强碱不期而遇,顿时
变作了抢建;一个无聊的人
仅仅是因为内心无料罢了。
而魏公村的阵阵秋风,不过相当于
四川土门村的某个人患上了
急惊风,却没有命中注定地
撞上他的慢郎中。
(2020年10月22日)
偶然想起
百骸通透啊,浑身轻松
这是中年时难得的少年身
身轻如燕啊,空气清澈
这是抑郁中少见的晴朗心
初夏的午后,那个八岁就懂得
把“高尔基的爸爸”倒过来读的顽童
何曾知晓四十多年后的
少年身和晴朗心
军军,我幼时的玩伴,语音微转,
便成鸡鸡,音同高尔基的“基”
此时想起你,便没来由地想起
那个初夏的午后
我和你,蹑足潜踪
偷窥邻家姑娘的睡梦
你说:她正梦见你张灯结彩
把她娶走
鸡鸡啊,前年在广州
面对那个请我们吃蛇的老板
你没来由地说起幼时的婚礼
突然间就哽咽了起来
(2020年5月2日)
歌
我把三十多年前听过的歌
一听再听。我再次听见:
潮湿的心头发出了滋滋复滋滋的声音,沉重又轻微
像金黄色的银杏叶,带着仅属于自己的弧线
轻轻飘零,配得上被我暗自赋予的称号——
叹息的形象代言人。
此刻,我很欣慰地看见三十多年前
那个忧郁的少年。他趔趄复趔趄,
搀扶着失败、激情和一小滴使性子的露珠
他忍住了眼泪、委屈以及
体型狭长的理想主义,径直来到
被雾霾锁住眉头的今天。
今天,那些苍老的歌
在肱二头肌里响起
在股骨里响起
在腓骨、结缔组织和汗腺里响起
但它们更倾向于盘旋在我的头顶。
我举起双手做投降状——
亮出的腋窝是两个天然的喇叭
它们一唱一和
正在反复播送我三十多年前
反复听过的那些歌。
(2019年12月2日)
敬文东,1968年生于四川省剑阁县,文学博士,现为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有《流氓世界的诞生》《指引与注视》《失败的偶像》《随“贝格尔号”出游》《事情总会起变化》《牲人盈天下》《皈依天下》《艺术与垃圾》《感叹诗学》《小说与神秘性》《新诗学案》《李洱诗学问题》《味觉诗学》《自我诗学》《絮叨诗学》等学术专著,有《写在学术边上》《颓废主义者的春天》《梦境以北》《网上别墅》《多次看见》《器官列传》等随笔、小说和诗集,另有《被委以重任的方言》《灵魂在下边》《诗歌在解构的日子里》《用文字抵抗现实》等学术文集。获得过第二届西部文学双年奖·小说奖(2012年)、第二届唐弢文学研究奖(2013年)、第四届东荡子诗歌批评奖(2017年)、第二届陈子昂诗歌批评家奖(2018年)、第十六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批评家奖(2018年);第四届当代中国文学优秀批评家奖等(2019年)。
崖丽娟,壮族,《世纪》杂志副主编。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出版诗集《未竟之旅》《无尽之河》《会思考的鱼》。被评为中国诗歌学会“2021年度优秀会员”并有诗歌获奖。在“南方诗歌”开设“崖丽娟诗访谈”专栏,诗歌、评论、访谈见于《文艺报》《文学报》《解放日报》《欧洲时报》《诗刊》《上海文学》《作品》《诗选刊》《诗林》《草堂》《中国文艺家》《百家评论》《安徽文学》《山东文学》《广西文学》《芒种》等。现居上海。
- 上一篇: 古代文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帮助我们更好地在今天生活
- 下一篇: 雷平阳:与聂权谈,十题
{Content}
- 信奉 23
 (2次)
(2次) - 咏怀 20
 (2次)
(2次) - 山宁 20
 (1次)
(1次) - 田字草 11
 (1次)
(1次) - 师红亮 10
 (1次)
(1次) - 季春孟夏 10
 (1次)
(1次) - 天涛 8
 (1次)
(1次) - 圣手书生 2
 (1次)
(1次) - 王兴发千文 1
 (1次)
(1次)
- 苍翠江南 246
 (11次)
(11次) - 信奉 188
 (8次)
(8次) - 晨笔 146
 (5次)
(5次) - 王伟丰 120
 (3次)
(3次) - 山丫草田 86
 (5次)
(5次) - 咏怀 65
 (2次)
(2次) - 鱼城烟雨 57
 (2次)
(2次) - 春无眠秋无言 52
 (3次)
(3次) - 周士强 48
 (3次)
(3次) - 赵昇 36
 (2次)
(2次)
- 杂感 46
 (3次)
(3次) - 青玉案.雨中游国清寺 42
 (3次)
(3次) - 成语系列之:事业燚燚 21
 (1次)
(1次) - 古风•清明祭与痛 18
 (2次)
(2次) - 遇见春天 15
 (1次)
(1次) - 七绝·南高学子在“紫荆杯”书画大赛创佳绩 12
 (2次)
(2次) - 重阳 11
 (1次)
(1次) - 七言绝句. 暮春 10
 (1次)
(1次) - 如梦令•夜色 10
 (1次)
(1次) - 游广州塔 10
 (1次)
(1次)
- 下雪 168
 (1次)
(1次) - 游桐花林 142
 (10次)
(10次) - 水龙吟·二首 140
 (6次)
(6次) - 一江春水·二首 120
 (8次)
(8次) - 除夕 105
 (2次)
(2次) - 古风•清明祭与痛 104
 (8次)
(8次) - 桐花落时子规啼 88
 (6次)
(6次) - 咏春 80
 (6次)
(6次) - 七言绝句.谷雨习俗 71
 (8次)
(8次) - 七绝三首.记白礁慈济宫保生大帝 65
 (4次)
(4次)
- “爱中华 爱家乡”2024中国农民诗会征集启事
- 中国作协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扩大)会 专题研讨新时代文学更好助力乡村振兴
- 世界读书日·东岳雅集——《当下的诗意》分享会在京举行
- 以理想的诗意编织乡村的模型
- 第422期“每日好诗”公开征集网友评论的公告
- 每日好诗第425期(旧体诗)入围作品公示
- 每日好诗第425期(现代诗)入围作品公示
- 2024第二届“天涯诗会”征稿启事
- 每日好诗第424期(现代诗)入围作品公示
- 以诗为媒,续写“山乡巨变”新故事
- 中国作协召开党纪学习教育动员部署会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扩大)会
- 每日好诗第424期(现代诗)入围作品公示
- 每日好诗第424期(旧体诗)入围作品公示
- 除了诗歌美学,还应强调诗歌力学
- 细节是诗意生成和传达的强大动力
- 2024“春天送你一首诗”征集选 |第九辑
- 致敬巨匠,百年诗情!北京法源寺百年丁香诗会今日开幕
- 第421期“每日好诗”公开征集网友评论的公告
- 海峡两岸诗人在漳共品四月诗歌诗与城市光影——2024闽南诗歌节在闽南师范大学开幕
- 2024年橘花诗会诗歌征集获奖名单公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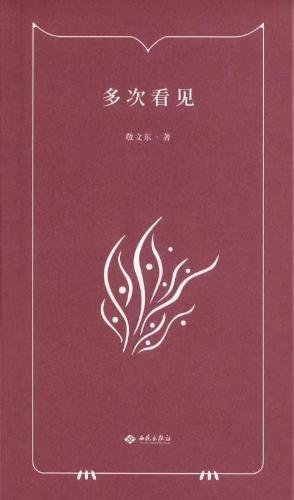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34246号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34246号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